1. 到了港島,便回不了九龍
「過海」[1],是很多香港上班族每日的例行公事。在張吻冰的小說〈粉臉上的黑痣〉(一九三○年)裏,也有一個談「過海」的小段落。小說的敘述者說,妻子的哥哥因住在九龍,來訪必須「經過舟車的跋涉」,不便在平日到訪「這小島」,所以往往選擇在翌日沒有工作的星期六見面,聊得太晚便乾脆借宿。[2]香港現在的交通非常完善,處處都是高速公路和鐵路,就算穿州過省也非難事;像張吻冰所說的這種到了港島,便回不了九龍之生活方式,似乎不再是我們可以想像的事情了。
我們對「香港」的印象,會隨時間不斷改變;例如,如何把「香港」分成「港島」、「九龍」、「新界」呢?「港島」、「九龍」、「新界」的分界規則,大抵以英國佔領香港土地的先後次序有關:先是港島,然後是九龍,最後便是新界——但這是香港上班族的想法嗎?似乎不是;因為我們更常以「日常」來感知「香港」。坐鐵路上學的,會以鐵路系統為界,籠統記住「地下鐵路」(MTR)是「港九」,「九廣鐵路」(KCR)是「新界」,於是有人誤把荃灣、將軍澳一腳踢入「九龍」;看地圖開車的,則會以地圖的鳥瞰視野為據,於是又有人以為大嶼山和長洲是「港島」的一部分。當代城市有關「空間」(space)的意義,就這樣從日常生活滲入我們的意識之中。[3]
2. 地景與文字
時至今日,我們仍會透過不同年代文學作品所描述的「香港」,來重認這城市的當下與過去。這些描寫地方的文學作品,如明顯以某地方為文本題材或主題,皆可稱為「地誌文學」(topographical literature)。雖然「地誌文學」這個文類(genre)名稱應衍生自西方文學研究;[4]但以描寫地方為題材或主題的作品,並非專屬西方文學的一時之物。李白有〈望廬山瀑布〉,蘇軾有〈前後赤壁賦〉,柳宗元有〈永州八記〉,歐陽修也有〈醉翁亭記〉,這些廣為人知的中國古典文學名作,皆為「地誌文學」。「地誌文學」大多強調寫實的價值。以香港文學為例,《中國學生周報》於1960年代末辦過名為「香港風情」的專輯,編者認為像舒巷城〈鯉魚門的霧〉這種以平凡人物展示現實的文本,就是富「香港風情」的作品,並強調「香港風情」就是「現實」的意思。[5]
「地誌書寫」(topographical writing)和「文學地景」(literary landscape),則是比「地誌文學」意義更為廣泛的術語。「地誌書寫」所指甚廣,可納入不一定屬於「文學」的文字,如地理文獻、航海日記或旅遊指南等;而「文學地景」可專指文學文本(無論是否以某地方為主要題材)中的地方書寫。[6]在文字、圖畫和影像——尤其是經典或暢銷作品出現的地景,都極具吸引觀看者「重返現場」的魔力。旅客來香港,都喜歡訪尋砵典乍街(石板街)、中區電梯、都爹利街和美都餐室等香港着名影視場景。偵探小說《福爾摩斯》在十九世紀末開始大賣,[7]當時的倫敦根本沒有「貝克街(Baker Street)221B」這個福爾摩斯住址;現在那裏已成為遊人駐足的「福爾摩斯博物館」了。
本書所有作者都以香港地方為創作主題,誠然屬於「地誌文學」的範疇;而其中描述地方的文字,就是「文學地景」。同樣指向現實,「地誌文學」與旅遊指南有何分別?這裏可以說的話很多,現在不妨只挑最顯眼的分別來看。
我們把旅遊指南弄上手,靠着指南的指路功能,看起來比較不容易迷路;「地誌文學」有時雖然兼具這樣的指路功能,但多不會以此為創作意圖。讀者讀到張婉雯在本書中所說的沙田中文大學檸檬批、蛋糕仔,嘴饞時得自己去找上山校巴的路線;而陳麗娟在九龍城的哪個字號買粿回家煎吃呢?這更是一個只有陳麗娟才能回答的問題。讀者只能一邊咀嚼,一邊想像文中小吃的味道——如陳麗娟說的「只能隨緣」。也許我們永遠無法嚐到作者筆下的相同味道;但在那閱讀文學地景的瞬間,我們總能想起,自己在青蔥年華裏的街頭美味和心頭滋味。
「地誌文學」比旅遊指南更為豐富,因它的文學地景蘊藏着書寫者的「地方感」(sense of place)。[8]文學地景的「地方感」,就是書寫者對地誌的情感。吳潛誠認為,書寫地誌的作品不是綜合的印象,而可予作者想像沉思;[9]鍾怡雯也點出,如地誌「偏向史料式的地理學觀察報告」,便不能構成「建構地方意義的地誌書寫」。[10]也就是說,「地誌文學」中的文學地景不只是追求客觀的地誌,而包含書寫者的情感。
本書的阿修談觀塘球場時,發現自己不再踏足舊地,只能改從「陳浩南」身上重識早已陌生的「藍田波地」。陳子謙談旺角書店時,也隨着近年網絡小說《那夜凌晨,我坐上了旺角開往大埔的紅VAN》的出版,而多添一抹小巴身影。[11]阿三探討葵青的空間意義時,嘗試模擬葵青居民的生活,最終認為不能以外來者的身分來理解居民如何「以身體介入空間」。這些文學地景,皆盛載作者對地誌之鮮明、無法由他人取代的感受。一般旅遊指南,不可能同日而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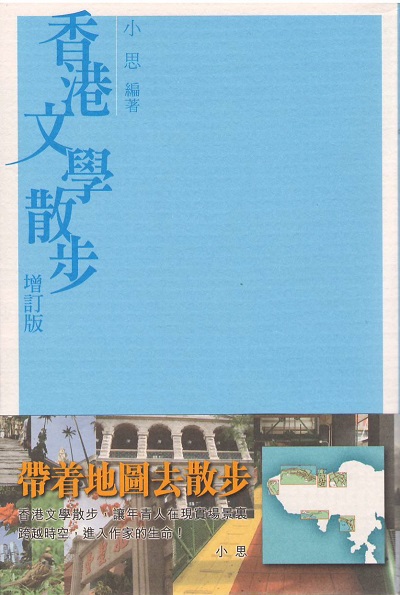
3.地景與對話
我們慢慢把「貝克街」變成「福爾摩斯住址」;把「中區電梯」變成「王菲偷看梁朝偉的小窗」。[12]這些地景讓我們經歷自己不曾經歷的日常生活,讓城市的感受變得越來越深刻和複雜,而且會隨時間而變濃或轉淡。
本書很多作者都採取「互文」(intertext)的寫作手法,以其他地誌文學作品或文獻入文,形成別人與自己,甚至自己與自己之間的地景對話;角度有別,風格百變,自成香港風景。陳德錦和鄭政恆的史料顯然較豐,對話穿梭古今;劉偉成邊走邊與「阿羣」侃侃而談,徐焯賢寫了一封信給「K」,鄧小樺在言談裏顧念「影子」,各有明顯的「對話」對象;梁璇筠、廖偉棠以自己的作品為觀照,與自我對談。每位作者在地誌書寫上的取材和筆法,各顯獨運的匠心。
作者筆下「香港」的文學地景,有時看起來獨一無二,讓我們一讀便知作者描述何方;有時卻在疑似之間,恍若是心有靈犀的感應。翻到唐睿的「到黃大仙祠燒香求籤」,我們曉得這個「黃大仙」指的其人、其祠、其地;[13]呂永佳的「參觀匯豐銀行」也讓我們認出「中環」,因為香港現在只有一所匯豐銀行,能令人產生「參觀」的念頭;看李凱琳的「大埔」和蘇偉柟的「柴灣」皆烙上鐵路痕跡,而鄒文律的「深水埗」、袁兆昌的「北區」同時細寫公營房屋,我們又感慨「鐵路」、「公屋」在香港的生活經驗裏實在舉足輕重。在作品的今昔風景中,作者不但與文本人物徐徐低訴,而且與讀者的香港記憶彼此喊話。
4. 地景與「香港文學」
文學地景創作與編選,每每呼應文學的主體形塑過程,兩者關係千絲萬縷。台灣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策劃「閱讀文學地景」出版計劃時,以讀者能從台灣地景來了解台灣文學為使命。[14]劉克襄在這出版計劃的推薦序〈打開地誌文學的窗口〉中也談到,這些文學風景「讓我們從人文的界面,開啟另一個新風貌的台灣認識,也豐富我在台灣的生活視野」,[15]可見文學地景對台灣文學界的吸引力。
「香港文學」選集,實也受文學地景所吸引。在《國共內戰時期香港本地與南來文人作品選:1945-1949》的〈三人談〉中,盧瑋鑾(小思)指出,南來文人作品「呈現出來的香港都市風情是很特別的[……],作品真實地保留了香港當時某階層的情況,如灣仔區、貧苦地區的真實生活面貌」;[16]而新近出版的《香港文學大系》系列,也收錄了不少包含文學地景的作品,如陳智德在《新詩卷》中編入李育中〈維多利亞市北角〉和黃雨〈蕭頓球場的黃昏〉,[17]危令敦在《散文卷二》編入夏果〈香港.船的城〉和蘇海〈電車社會〉等,[18]皆可見香港文學研究者對文學地景和地誌文學的重視。
張吻冰在〈粉臉上的黑痣〉的文末,記下這小說的成稿地點是「雪萊街畔」。[19]未知本書的十八位作者曾經在哪裏坐下來,走筆縷述心目中的「香港」?這十八篇散文,也許是在香港寫成的,也許不是;而肯定都像小思老師的《香港文學散步》那樣,滿載地緣,滿載人情。[20]

注釋:
[1]「過海」泛指往返香港島與九龍至新界,如「過海隧道」、「過海的士」等,但較常指「往香港島」,如「市區的士」(紅色的士)又稱「過海的士」,是「可以往返香港島的的士」。
[2]張吻冰:〈粉臉上的黑痣〉,《島上》第2期(1931年10月),頁2-3。小說寫於1930年6月18日;見《島上》第2期,頁28。
[3]陳國球曾於《香港文學大系.總序》中指出,「香港人」是「香港」地方意義生成的關鍵:「『香港』由無名,到『香港村』、『香港島』,到『香港島、九龍半島、新界和離島』的合稱,經歷了地理上和政治上的不同界劃,經歷了一個自無而有,而變形放大的過程。更重要的是,『香港』這個名稱底下要有『人』;有人在這個地理空間起居作息,有人在此地有種種喜樂與憂愁、言談與詠歌。有人,有生活,有恩怨愛恨,有器用文化,『地方』的意義才能完足。」詳參陳國球:〈總序〉,陳智德主編:《香港文學大系一九一九—一九四九.新詩卷》(香港:商務印書館,2014年),頁19。
[4]詳參Robert Arnold Aubin, Topographical Poetry in XVIII-century England (New York: 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1980), John Beckett, Writing Local History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c2007).
[5]編者:〈香港風情引——代編後〉,《中國學生周報》第810期(1968年1月),第6版。
[6]「地誌書寫」(topographical writing)和「文學地景」(literary landscape)分別衍生自人文學科研究常用術語「地誌學」 (topography,或作「地誌」)和「地景」(landscape,或作「景觀」)。「地誌學」為測量、描繪地形的技術,而「地景」本專指特定以繪畫藝術裏以地理風景為題材的作品;詳參J. Hillis Miller, Topographies(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Denis E. Cosgrove, Social Formation and Symbolic Landscape(London: Croom Helm, 1984)。文學研究中的「地誌」借用地理學繪製地圖的地名(toponym)命名意義,把作品指涉的地名看成作者與讀者約定的符號,並以「文學地景」(literary landscape)指認文學作品內關於已命名之地的文字。在華文文學研究裏,「地誌」、「地景」、「地理」大致通用;可參林淑貞:〈地景臨現——六朝志怪「地誌書寫」範式與文化意蘊〉,《政大中文學報》第12期(2009年12月),頁159-193;鍾怡雯:〈從理論到實踐——論馬華文學的地誌書寫〉,《成功大學中文學報》第29期(2010年7月),頁143-160。
[7]亞瑟・柯南・道爾(Arthur Conan Doyle)著,李家真譯注:《福爾摩斯全集》,(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3年)。
[8]地誌書寫生中的「地方感」(sense of place),是能從「地方」(place)的角度去考慮人與所在地空間的關係,而呈現「人類與世界連結的先天能力」,包括「對地方位置的準確認識」。詳參J. Hillis Miller, Topographies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文學研究中的「地方感」,通常指書寫者對地誌的主觀情感。
[9]吳潛誠:〈地誌書寫.城鄉想像 楊牧與陳黎〉,《島嶼巡航:黑倪和台灣作家的介入詩學》(台北:立緒文化,1999年),頁83-84。
[10]鍾怡雯:〈從理論到實踐——論馬華文學的地誌書寫〉,《成功大學中文學報》第29期(2010年7月),頁156。
[11] Pizza:《那夜凌晨,我坐上了旺角開往大埔的紅VAN》,香港︰有種文化@Sun Effort,2012年。
[12]「中區電梯」為香港電影《重慶森林》(王家衛執導)的主要場景。
[13]香港深水埗呈祥道尚有另一座黃大仙祠,或稱「黃大仙祠元清閣」。
[14]文建會(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出版前言〉,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策劃主辦;聯合文學出版社編輯:《閱讀文學地景.新詩卷》(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2008年),頁8。
[15]劉克襄:〈打開地誌文學的窗口〉,同註14,頁11。
[16]鄭樹森、黃繼持、盧瑋鑾:〈三人談〉,《國共內戰時期香港本地與南來文人作品選:1945-1949(上冊)》(香港:天地圖書,1999年),頁22。
[17]陳智德主編:《香港文學大系一九一九—一九四九.新詩卷》(香港:商務印書館,2014年)。
[18]危令敦主編:《香港文學大系一九一九—一九四九.散文卷二》(香港:商務印書館,2014年)。
[19]張吻冰:〈粉臉上的黑痣〉,《島上》第2期(1931年10月),頁28。「雪萊街」應為現在的中環「些利街」(Shelley Street)。
[20]原文為「《香港文學散步》改了新的面貌,仍滿載人地情緣,我盼望它能傳遞『歷史有情,人間有意』的訊息。」見小思:〈後記〉,《香港文學散步(增訂版)》(香港:商務印書館,2009年),頁203。
* 轉載自鄒芷茵:〈導言二 文學地景的趣味與價值〉,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文學研究中心編著:《疊印:漫步香港文學地景.一》,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2016年,頁xv-xxiv。
* 誠蒙作家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