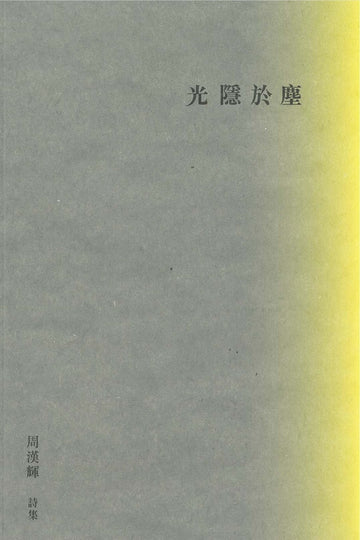在現當代語境的氛圍下,當提及「視覺性」,人們自動聯想起電影、電視產業。無可否認,這是當代藝術的潮流趨勢,然而視覺性的形塑未必單單與影像構上關係,乃與文字產生微妙的關係。
羅崗老師論及「視覺『互文』」的文章,指出「技術化觀視(the technologized visuality)」是「通過現代媒體、幻燈、電影等科技和機械運作而產生的視覺影像」,這種技術化的影像使得改變人們感知世界的方式,從而帶給人們一種「巨大的震撼性視覺體驗」──重建了觀眾與置身其中的世界之間新的「想像」關係和「批判態度」。換言之,視覺性的震撼能帶給人們新的想像與社會的反思,即表示視覺性與社會有密不可分的關係。除此之外,羅崗亦肯定「視覺互文」在二十世紀早期中國現代文學中具備巨大的視覺潛力。[1] 另外,亦有論者述及:「文學本身有着內在的顯像功能」,因為文學是通過語言藝術、時間藝術,訴諸心理和想像,因此文學具有視覺性。[2]
就着以上的論述,我認為文字文學同樣可以具備視覺性,作者可以從文字構建一個社會、生活的景象,形塑巨大的視覺力量。本文欲從香港詩人周漢輝[3] 的詩集《光隱於塵》(下稱《光》)分析其詩作的視覺性,並由此探索作者在作品中描繪的生活與社會,以及他筆下生死意象之呈現。
一、概述《光隱於塵》的風格及其在學界的研究方向
詩集《光》共有四十六首詩,分三輯,包括「塵」、「光」及「隱」。作品大多採材於社會及生活,語言平實自然,意象大致輕盈,但隱含着深刻的哲思。現存學界對《光隱於塵》的論述不多,但大致着重分析其「鏡頭運用」、「生死意象」及「宗教意象」。除此之外,周漢輝喜用敘事技法,例如詩人韓褀疇評論他的敘事技法是取自電影,[4] 正如他在訪問中說:「我很喜歡侯孝賢導演曾說到的『藝術就是距離』⋯⋯距離令你看得更清楚。」;[5] 另外,詩人鍾國強分析其詩作〈姑姑〉時,亦不難發現作者以第二人稱增加敘事距離。[6] 由此可見,《光》大部份詩作偏向敘事性,而這與電影的鏡頭運用有關。似乎,敘事詩比其他風格的詩(超現實詩類、抒情詩類)更能結合生活,而不沉悶地陳述事件,因此其文字的可讀性、吸引力如同影像的視覺性般龐大。
二、鏡頭運用的表現手法
在電影中,鏡頭運用是電影的表現風格,可以是蒙太奇(montage)的剪接技巧,又或是一鏡到底的長鏡頭(long take),無論哪一種技巧也好,均與創作內容相關。將鏡頭運用的表現手法放置於《光》的文本中,可見處處均呈現着電影的技巧。
在〈阿們〉一詩,詩人運用了空鏡頭。[7] 詩中寫到:「道別了,你留步/獨自凝看天花板漏滲水滴——/牧師頻頻在胸前劃十架/你卻一再分心偷看靈柩旁/一朵水花起起滅滅」。[8]詩人鍾國強稱此空鏡頭之運用當有「借物喻情、引發聯想」之作用。[9]的確,水花的起滅能讓人聯想起生死。但事實上,詩中的「煙霧」、「閃電」、「川流」等意象,亦運用了空鏡頭,呈現出生命短暫之弘外之音,其作用在於可將時間拉長,呈現出電影感,使讀者能浮沉在作者的思緒之中,這就所謂的電影視覺性。除了〈阿們〉一詩,空鏡頭的運用亦見於其他詩作,例如〈大美督環保行〉、〈禱詩〉、〈船渡漫筆〉及〈再見方舟〉等。
另外,詩人在〈迴轉〉一詩中運用了蒙太奇剪接技巧。整首詩密度很高,包括三個場景,例如「壽司店」、「安老院」及「小聖堂」,可見詩人反覆變換場景,而靠食物聚焦在「你」的身上。「你」是一名單親媽媽,任職安老院職員,負責為老人清潔洗澡,但地方卻在「老樓天台」,老人需要赤身露體,最後被「長焦距鏡頭」拍下,然後安老院倒閉,「你」就失業了。詩作共有五處蒙太奇剪接,以下略舉兩處:
第一處:
軍艦壽司航去,你喝一口熱茶
杯中霎餘風暴與閃電──擱下(壽司店)
杯子筷子,純熟戴起手套口罩(老人院)
一列老人早脫光衣褲,向你蠕進[10]
第二處:
趕忙代洗髮膚,也急於通便
你抽回指頭,糞污沖入渠洞
喚下一位,再下一位──三文魚
你待得一碟肥美,跟女兒對吃[11]
這處的變換在破折號前後,從老人院跳回壽司店。除上述的場景變換外,詩作還有從壽司店轉入老人院,再從老人院跳入小聖堂等。其實詩題已暗示了蒙太奇剪接的手法,既指涉輪迴壽司,亦指涉「你」人生的迴轉。[12] 「迴轉」一詞就如輪迴接合,亦隱喻人生輪迴之意。此詩可見詩人刻意運用視覺性的技法融入詩作,好處時讓人有畫面感,壞處在於全詩並無分節,敘事緊密,令人容易失焦。雖然詩人故意用破折號提醒讀者場景轉換之處,但在閱讀此中篇幅的詩時亦難以聚焦。就像何福仁評其〈守山人〉,形容收結卻「過於戲劇性」,指出周漢輝之作品「美中不足的是,稍嫌意象繁密,像搖得很厲害的鏡頭,反令焦點模糊起來。」[13] 但整體而言,此詩能夠從電影的剪接技巧表現出視覺性。
最後,承韓祺疇的說法,詩人在〈無傷〉一詩運用了「倒向回轉鏡頭的方式」[14] 呈現,而嚴瀚欽稱此為「倒帶式寫法」。[15] 簡言之就是時光倒流,呈現非現實的場景。全詩的故事是「你」在一場塌樹意外中死去,鏡頭的安排是從結果回溯至最初,亦即是「細雨後街燈亮起,你/也醒來,向光點了點頭」是已經死亡的「你」。而在這平凡不過的描寫之後,你可發現詩句「把胸骨塞回皮肉下了/打呵欠止血,打噴嚏吹掉傷痕」、「卻見葉子飛回枝頭,你仍守着崗位」、「斷樹們一一接合自己」[16] 等,均可以察見作者運用倒向回轉的鏡頭,把時間逐漸推回至意外之前。於是,本來已死的你,卻死而復生,成就了詩題〈無傷〉,這涉及生死的辯證將在下文處理。由此,這種運用電影的鏡頭表現手法,再次出現在周漢輝筆下,呈現出其詩的視覺性。
在上述的分析中,可見詩人運用電影鏡頭的方法於詩作之中,例如蒙太奇、空鏡頭及倒向回轉鏡頭等,一一讓讀者在腦海呈現出電影畫面、鏡頭感,表現出詩的視覺性。因此,一如羅崗的說法,在攝影和電影的視像衝擊底下,作家們才有了對「文學本身的思考」,繼而「文學必須進行自我設計」。[17] 所以,文學若能產生視覺性力量,亦可奪得大眾的歡心。
三、空間意識
在此章,我欲從空間意識分析《光》。所謂空間,並不是一個物理存在的空間,而是作者在文字中所締造的想像空間,這與電影的空間意識大同小異。攝影機在景物安排之不同,會出現不同的情況,例如「凡景物距離愈遠,它的形象就會變得愈小」或「凡在視線以下的景物,距離愈遠,影像的位置便愈高」。[18] 以上情況,均與物理學有關,亦即是說穿了電影與科學科技的關係密切。但是,我們在觀看電影時仍然感受到其空間感,這是導演的有心安排,使其呈現隱喻及其電影美學觀。同樣道理,詩人周漢輝亦在其詩作中設計了不少空間,上文已提到他喜用第二人稱,可增加距離感,由此推測,詩人在設計空間時,應會考慮距離感的同時,保持敘事不失焦。
且看運用中景(medium shot)的詩,例如〈晨歌〉。全詩散文式敘事一筆到底,沒有分節,焦點人物是「你」和「她」,故事暗示了這二人是情侶──「給爭吵對罵後的彼此」、「她搖頭,伸手抱你」。場景共有三個變換:家裏、茶餐廳及街道。詩人在敘描的時候,運用了中景的鏡頭,為描寫對象締造空間:
花瓶碎片,然後是鬧鐘的時針
與刻度。你在清掃,她取來
兩雙拖鞋,給爭吵對罵後的彼此⋯⋯
你背起重囊,她喝光你喝不完的
黑咖啡。茶餐廳外年輕的父母
輪流抱帶親兒,肩背上手
伸來,走遠,伸來,走遠,拐失在
你們的眼角──一泡狗尿撒開[19]
先看第一個片段,這是情侶二人在家裡吵罵過後的場景。一人在清掃,另一人在取來拖鞋。詩句能為我們繪製出二人共處一景框,同時進行不同行為的影像,而且是流動。第二個片段則發生在餐廳內外,先敘述情侶,後描述餐廳外年輕父母抱帶兒子的忙碌。由此,詩句製造的影像是聚焦情侶,但模糊後方的年輕父母。兩個片段,詩人有度地把兩人放置在同一個景框之中,而共同的是呈現運動性,這亦是電影鏡頭的常用手段。
另一首〈三色蛋〉,則運用特寫(close-up)的鏡頭。全詩共三十二行,沒有分節,詩人主要表達時間流逝、成長的主題。詩句中寫到「火水爐火前打蛋、切碎皮蛋/和鹹蛋、拌勻、下水和油」,[20] 這無疑是特寫了父親煮食時的手藝,然後畫面一轉──「放涼了,你便老起來」。從特寫的景頭及時空之變換,突出的時間、成長的主題。再者,此詩並不單止運用了特寫鏡頭,還運用了中景:「像停電前你準備開動/抬頭前望以為/那男孩還埋首吞吃三色蛋/老食堂沒有別的食客」。[21] 整個景框便包含了「你」和「男孩」,還有餐廳的空桌,所以可見詩作所呈現的空間感是具有運動特性。
還有一首更有趣味,直接把「導演」帶進詩句,形成戲中戲的畫面。這首詩詩題為〈默字光言──給關本良導演及書店店主樹單〉,全詩描寫了「你」在導演的指導下拍攝鏡頭,但因很多「質疑」而「叫停」,於是「你」的靈感就湧出來──「你的靈感/恰隨紙屑漫降,像雨後放晴」。[22] 導演在指導鏡頭的時候,他便為影像架構空間,而詩人在書寫的同時,亦描述周圍的擺設:「為最後一個鏡頭/攝影師疊起書來,承托攝影機/伏地操作時,燈光師多架一支/燈臂,嵌燈泡,美工正在燈下/掛起一幅燙金色紙,搖創出金浪」。[23] 亦是為詩佈局,構成詩人所知所感的空間,可見,詩人與導演均擁有空間意識。
從上述的文本分析之中,可觀察到周漢輝之所以用第二人稱作為主要的敘事視角,一方面可使讀者與人物增加距離感,另一方面更方便詩人使用電影鏡頭的技功構建其空間。詩人具有如此敏銳的空間意識,亦成為了他文學風格之特色,無疑是其詩的視覺性之呈現的技藝。
四、生死意象
生死意象在《光》涉及頗繁,這與周漢輝的親人,乃至時下社會有關。詩人就生活與社會兩方面採材,融入電影的表現手法,錘打出極具穿透性的詩,構成其筆下的社會群像。以下將從〈無傷〉、〈落葉樹〉、〈姑姑〉及〈約定的遠行〉等四首詩作分析。
先看〈無傷〉及〈落葉樹〉,此兩詩有共同的意象──「落葉」與「樹」。〈無傷〉在上文已分析過其鏡頭的藝術手法,於此,兩首詩均道出一個命題:生死無常。落葉和樹作為意象,前者可視為生命的完結,而後者可視為永生。「傷痕」及「創口」分別是二詩的用詞,但留意詩題,卻非常正面,與死亡毫無關係。〈無傷〉一詩的主角因替工已被塌樹壓死,隱喻人生無常的主題,但詩人卻以「細雨後街燈亮起,你/也醒來,向光點了點頭」[24] 形容他的死亡,似乎詩人把死亡看得很淡,而死亡其實是重新,死亡就像詩人般輕描淡寫一筆而過,不是甚麼痛苦。說得也對,死亡那一刻很快,對比人生的磨難,根本就不可相提並論。那〈落葉樹〉呢?詩中所描述的痛苦,如「淚水」、「血」、「痛雨」等只是「刺癢」,不足掛齒,然而落葉還在「打轉」和「晃蕩」,象徵生命的進行。詩的最後兩句形成強烈的對比,予人反思:「站立祈禱,不見葉落腦後,你代接/枯亡,塵體蠢蠢爬過葉脈與掌紋」。[25] 葉脈與掌紋相似,就好像命理,落葉的枯亡最後被塵附染,而你的掌紋亦是。暗示死亡每天發生在大自然之中,而你也將有此一天。即便如此,詩人刻意用「塵體爬過」,這種生命力的意象,恰好與死亡對比,亦即隱言着生死如出一轍、輪迴往覆。
〈姑姑〉、〈約定的遠行〉二詩均充滿宗教及死亡的意象,前者有「主日」、「教會」、「聖餐」和「靜禱」;後者有「十架」、「祈禱」、「福音」、「主餐」及「神」等意象。這二詩似乎指涉着西方的宗教。另外,詩句「身體需要一個傷口永遠張開」(〈姑姑〉)、「十架上血風乾了」(〈約定的遠行〉)均象徵着死亡。因此,先可預視詩人常把死亡及宗教置在同一首詩之中,以宗教永生之觀念撫平死亡所帶來的傷痕。例如〈姑姑〉一詩主要以「茶」及「水」隱喻姑姑在危疾時的痛厄與逝亡。誠如鍾國強所言,「像茶漬化開」暗示姑姑已經離世,至於「水」,則前喻為一種苦痛的淡化,更進一步隱喻時間之流。[26] 且看〈姑姑〉相關詩句:
你眼紅了,她還以開 ,化開
杯中濃苦──甜成主日的葡萄汁⋯⋯
雨水急打車窗,你坐在餐椅上淌淚
原來姑姑走到身旁,彎腰,遞來紙巾
你拭去了,水,拿起傘子下車
風雨淘洗着茶樓的玻璃牆,姑姑
像茶漬化開,融進餐桌及燈光中
你穿過,玻璃觸及你即流為水
一隻水把你自水中拉起,完成了儀式
姑姑還像記憶實在,看你的眼裡有閃光[27]
從這可感受到,「你」和姑姑形成軟弱與堅強之對比:「你」難以接受姑姑死亡的事實,可面對死亡,姑姑表現得樂觀,更把杯中濃苦化開,變成甜的葡萄汁。而「水」則是救贖的象徵,後來作者完成了浸禮,好像用水就能化解傷痛。對此詩,吳美均評論道:「這首詩以多重視角寫,使死亡在重重互換的視角關係中多了一份對世情濃重而化不開的關注。」[28] 另一首詩〈約定的遠行〉,則每每在作者生病、恐懼時(板縫間一滴餘血縱橫滲成,你虛脫前/虛劃十架),[29] 就轉入「十架」與「阿們」的宗教詞彙,使之心靈就得到安撫,詩末一句「太初,神創造天地」[30] 化用了《聖經》經文,彷彿將所有生老病死之痛苦回歸天地最初,使我不禁猜想:詩人應該有超脫的一面。
綜上所述,從分析詩人周漢輝的詩集《光》所見,不難發掘他運用了電影的鏡頭入詩,亦即他為詩製造了作者的視角,同時賦予讀者一個虛構的電影視角,以便讀者像觀看電影一般走入詩人的世界,體察詩內的情味和哲思。詩人用詩(文字)構造一個個電影畫面,無疑是充滿視覺性,而這種視覺性的力量之衝擊不亞於電影本身,惟讀者需要注意場景變換的詩句,那就能掌握作者的思路。就《光》而言,詩總帶有視覺性,文字過渡至影像,經過咀嚼,又回歸文字本身,而詩人筆下的人物,大多為低下層及關於一些厄苦,直接表達作者對草根之關注,而透過這些敘事,進而在詩中書寫生死命定的主題。
注釋
[1] 羅崗:〈視覺「互文」、身體想像和凝視的政治──丁玲的《夢珂》與後五四的都市圖景〉,《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7卷5期(2005)︰36。
[2] 金華:〈略論文學的視覺性〉,《重慶教育學院學報》第24卷第5期(2011)︰81。
[3] 作者簡介:周漢輝,基督徒,畢業於香港公開大學。寫詩與散文。曾獲得青年文學獎、李聖華現代詩青年獎等多項本地文學賽事冠軍,並於海外獲得台北文學獎、新北市文學獎、宗教文學獎、金車現代詩網絡徵文獎等。2015年獲香港藝術發展局頒發藝術發展獎——藝術新秀獎(文學藝術);2018年獲邀代表香港赴美國愛荷華大學參與國際寫作計劃。著有詩集《長鏡頭》、《光隱於塵》。〈作家訪問片段——周漢輝〉,賽馬會「觸境生情」虛擬實境中國語文教學計劃,http://www.jc-vr-chinese.hk/index.php/author-chow/(讀取日期:2023年5月1日)。
[4] 韓褀疇:〈角落裡一雙眼睛正好斜望你:敘事詩作的鏡頭運用──以詩集《光隱於塵》為例〉,每天為你讀一首詩,https://cendalirit.blogspot.com/2021/02/20210220.html(發佈日期:2021年2月20日;讀取日期:2023年5月1日)。
[5] 黃柏熹:〈凝望城市的「沉默」人物──訪詩人周漢輝〉,《虛詞》,https://p-articles.com/heteroglossia/1108.html(發佈日期:2019年11月4日;讀取日期:2023年5月2日)。
[6] 鍾國強:〈結束與開始,天上與人間──讀周漢輝的〈阿們〉,載於周漢輝:《光隱於塵》(香港:石磬文化有限公司,2019),149。
[7] 「在影視中,抒情蒙太奇是一種在保證敘事和描寫的連貫性的同時,表現超越劇情之上的思想及情感。最常見就是在一段故事敘事場面之後,恰如其分切入極具象徵意味的空鏡頭。」詳參胡玉梅:〈中國現代詩歌中的電影技法探析〉(湖南:中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0),29。
[8] 周漢輝:〈阿們〉,《光隱於塵》,139–140。
[9] 同前注,150。
[10] 周漢輝:〈迴轉〉,《光隱於塵》,39。
[11] 同前注,39。
[12] 韓褀疇:〈角落裡一雙眼睛正好斜望你〉。
[13] 關夢南編:《李聖華現代詩青年獎作品集2017》(香港:白綠出版社,2018)。
[14] 韓褀疇:〈角落裡一雙眼睛正好斜望你〉。
[15] 嚴瀚欽:〈被消失的痕跡──讀周漢輝〈無傷〉〉,《虛詞》,https://p-articles.com/critics/2631.html(發佈日期:2021年12月16日;讀取日期:2023年5月2日)。
[16] 周漢輝:〈無傷〉,《光隱於塵》,34。
[17] 羅崗:〈視覺「互文」、身體想像和凝視的政治〉,37。
[18] 林年同:《中國電美學》(台北:允晨文化,1991),68。
[19] 周漢輝:〈晨歌〉,《光隱於塵》,82–83。
[20] 周漢輝:〈三色蛋〉,《光隱於塵》,16–17。
[21] 同前注。
[22] 周漢輝:〈默字光言〉,《光隱於塵》,59–60。
[23] 同前注。
[24] 周漢輝:〈無傷〉,《光隱於塵》,頁34。
[25] 周漢輝:〈落葉樹〉,《光隱於塵》,頁89-90。
[26] 鍾國強:〈茶與水,那些消逝中的光影〉,144–145。
[27] 周漢輝:〈姑姑〉,《光隱於塵》,113–114。
[28] 吳美筠:〈複調與多重視角的生死相聚〉,載於周漢輝:《光隱於塵》,160。
[29] 周漢輝:〈約定的遠行〉,《光隱於塵》,115–116。
[30] 同前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