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覺得自特朗普選上美國總統(2017年)後,人類更傾向以暴力衝突來壓下(不是解決)糾紛。結果就是肢體受傷多了,打交輸了不服氣,表面妥協求和解,壓抑的負面情緒只是等下一個爆發點。這是眾所週知的常識,各人又似乎選擇視而不見,是否各自儲備資源再大打一場?不得而知。巴特勒(Judith Butler)在2020年出版的《非暴力的力量》(The Force of Non-Violence)一書中倡議:假設人類仍是尊重弱勢生命的話,我們就應(儘快)建造一套對抗暴力的「非暴力」話語。
「以暴易暴」可以自停嗎?
巴特勒先討論「暴力」的定義。他認為暴力不應單指(非同意的)肢體接觸(如血腥毆鬥),亦包括系統性的歧視壓迫(無法理的不容許他人街頭拍攝、族內歧視等)。暴力也是脈絡性的產品(為錢財碎屍犯法人神共憤,殺敵人保家衛國戰爭英雄)。施暴者通常都有自以為是的理由証成自己的行為,標籤他者為「崩壞份子」──美國白人警察暴力對待非白人市民時,總說對方屬於高危疑犯類別;同理,市民在血腥對抗警方時也會指對方不辨是非、毫無公義感,只懂以過份暴力鎮壓(當然不是手無吋鐵的)市民。在此種暴力生活化的氛圍中,非暴力並不是一個選擇,「以暴易暴」就是全人類毫不懷疑的日常執念。事情至此,暴力已進化為不知起點終點的永恆輪迴。暴力衝突越來越來越來越多,憤恨有增沒減,堅持以暴易暴的各人是否仍然清楚知道甚麼時候該停手?是當所有高危份子消失於天與地的一刻?還是由反警人士自身化作警察才是完美結局?眾生真的肯定到時社會會更平和安全?此種初心能否堅持不改?還是,暴力會自我生長反過來控制人類?
暴力迴戰中各人只係獨立個體?
其實當刻大家都心底明白:暴力衝突的各方(及其支持者,甚至充作中立者)之間,總有千絲萬縷切不斷的關聯—以往的同系同學、今日的情侶、甚至相處半生的家人都因暴力循環而決裂。巴特勒在書中提出的第一個警醒就係:沒有人是生存在真空的完全獨立主體。如果非暴力本質上比暴力高貴有美感的話,那就是因為此生活態度並非着眼於個體,而是平等的社會關聯。非暴力於是成為自以為是的暴力最有效反抗。試想:當大家缺乏冷靜徹底的自我質疑一剎那,就因一時血氣上腦殺紅了眼,狂亂暴打另一生物,或與曾互相親密關心的死黨愛人父母完全翻臉成陌路仇人,真的值得?真的是體現公義?
巴特勒強調此種平等關聯重點是互相依賴(interdependency);憑着此信念,我們在任何時候(包括暴力時代或瘟疫蔓延時),也要不斷自我詰問:究竟有沒有生命比另一生命重要?衡量標準是甚麼?此兩問題相當重要:當眾生明白互相依賴是重要時,我們同時也是承認並面對自己的不足與可悲(grievable);當我們既是如此不堪,又是否有資格有基礎指評其他人的價值比較低?假設長洲今日有強烈的獨立聲音,明日天馬艦就不顧一切派強兵鎭壓,並宣稱「寧願今日死一兩千人,總好過將來真的有大規模衝突死幾萬」;會否有戰爭是未知數,但長洲居民與香港各區市民總有不少不弱的互動關聯,憑甚麼理由說已死的這一兩千人比較值得犧牲?再簡單直接的說,由此而生的怨恨會壓下尋求獨立聲音,還是令長洲居民更憤怒更想千方百計見縫插針組織對抗?
為甚麼人始終嗜殺(他人及自己)?
巴特勒亦企圖在書中解答「為何有人會這樣喜歡以暴力解決意見衝突?」這問題。他引用弗洛依德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分析,指出暴力破壞的不只是另一(群)人的身體;更重要的是限制暴力的機制關卡──人類建設文明不就是要捨棄蠻荒時期以暴力定勝負的方法嗎?(頁154)弗洛依德於是提出「死亡驅力」這概念──這種不斷慾望與被閹割的原物(The Thing,拉康用詞)重新結合的心理動力具有不可預估不可理喻的破壞力—此種心理動力會令人不知不覺做出破格的事:如足球賽事中守衞莫名奇妙在自己隊的禁區用手檔球、已婚多年小男人會突然出軌搞一夜性。它可以令一個國家(暫時)上下一心放下異見為了自己都知錯誤的借口全力與他者奮戰(電影《木馬屠城記》中的特洛伊人民及軍隊),當然亦可令同一地區人民撕裂互相屠殺(見以上長洲的例子)。死亡驅力可以癱瘓人類的理智道德自制及自我批判能力(即超我,Super-ego);所以,我們才會在血腥暴力後悔咎之前一時失智破壞淨盡人人親䁥關聯。
按巴特勒的分析,超我可以是對衡死亡驅力的暴力,能夠不容許死亡驅力引發的破壞力外溢。然而,超我過強又易引致主體自毀(電影《屍殺列車》中孔劉飾演的主角不就是怕自己變身不受控制的喪屍而自殺嗎?我們有否見過士兵目睹同伴被屠殺後憤而衝鋒陷陣但求一齊犧牲?)弗洛依德認為唯有「狂躁」(mania)可以平衡各種心理暴力。)弗洛依德在《哀悼與憂鬱》(Mourning and Melancholia)一書說明,當主體沉溺傷心時,狂躁企圖切斷主體與已逝者的關聯,是對過強超我(對已逝者的無節制思念與過份傷感)的反擊。狂躁具有與超我不同的批判力,足以在超我將會催毀主體時,分隔兩者。狂躁令主體脫離超我建構的現實(執着於同歸於盡不是唯一選項),並依賴(曾)被(過強)超我攻擊的慾望想像其他生活的模式方法。
平等、公義、法律三者關聯需更多討論
綜觀而言,巴特勒的非暴力話語先由質疑暴力的定義開始:既然暴力是論述產品,權力自是不穩定缺乏單一源頭,不能簡單自我定義為永恆強/弱勢。他強調的是人與人之間的平等、關聯及可悲。話語最後一個警醒就是抽離:各人應從情緒爆發中抽離並尋找非暴力的生存方法,不能被暴力利用。
此書極力攻擊個人主義,蔑視以自由主義為基礎的法律體制,當然巴特勒不會支持取消法律,但也不反對公民抗命。問題又回到是否只有違法才可呈顯法律的極限呢?如果公義是量度法律的功具,巴特勒並沒有在此書仔細探討平等與公義的定義及關係。事實上,平等(可悲性)並不一定是公義──以同一標準對待能力、背景、資源有差異的人就是平等?給予今天的弱勢特別保護(如設強制舉報機制保護兒童)就是公義?還是眾生就應不停在當刻宰制邊緣反省?巴特勒跳過有關探討就直接指出平等不是人與人的比較(香港反歧視法律的基礎),而是結構上的公義──此種論辯太過跳脫粗疏。
《非暴力的力量》以美國為背景,可否適用於世界其他地方要詳細討論;但明顯未足以改變美國境外情況。特朗普已下台幾年,全球輿論缺了挑釁言論似乎平和了;實際上,歐陸戰爭未見完結可能之餘,美國國內校園開鎗情況又有否減輕?癥結可能就是反反省反理論,而是死亡驅力就是強大,眾生感覺打就是爽。又挫敗又痛苦的是:如果打完、讀此書後,仍然執意要選擇暴力的話,提出復和再出發又有何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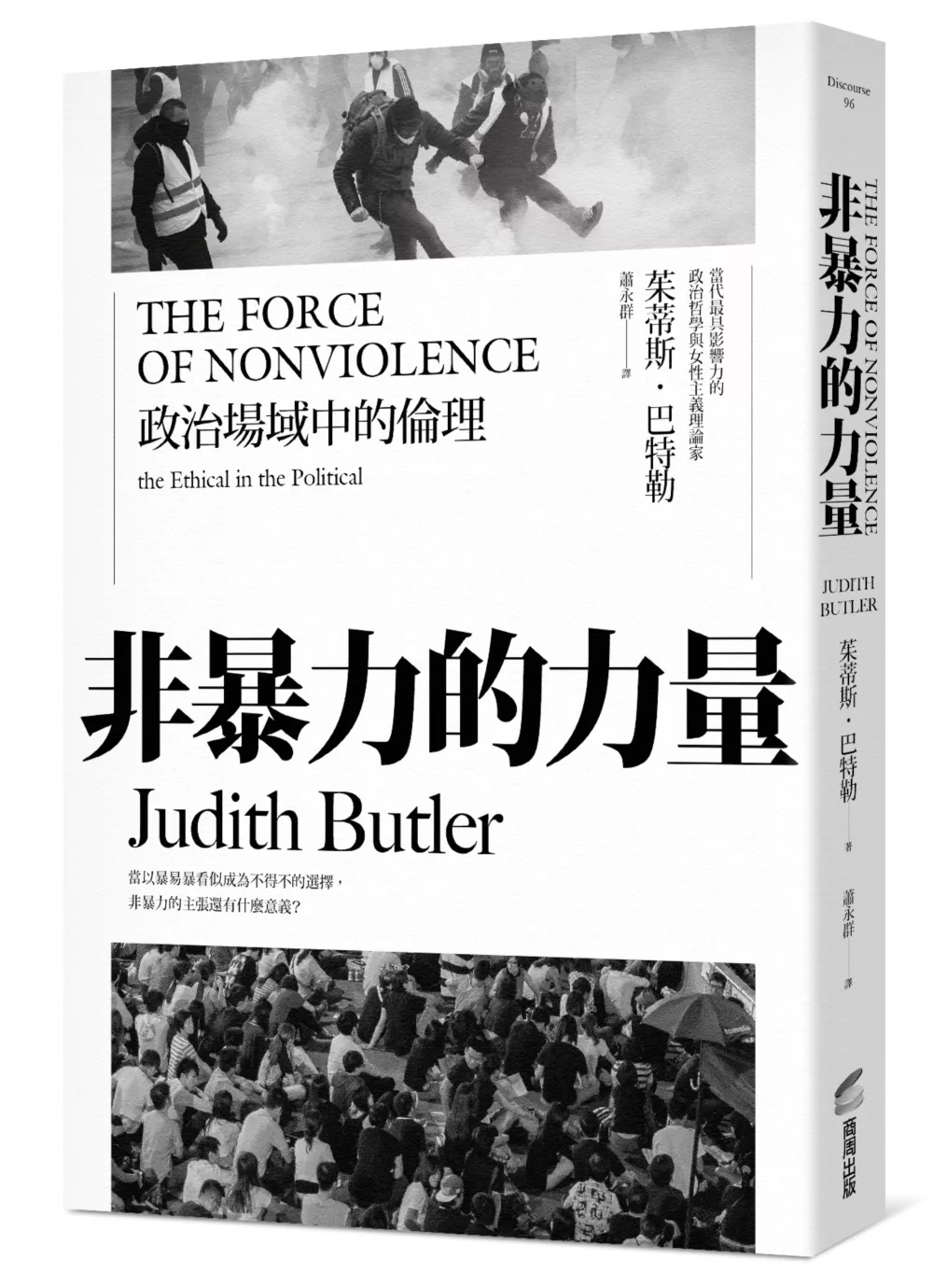
A very good book comment, Thank you very mu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