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與跨文化現代性》這本書是張歷君歷經十年才修改完稿付梓問世的學術力作。書名中的關鍵詞「跨文化現代性」值得深思。在此書導論中,張歷君勾勒出從瞿秋白與跨文化現代性之間的關係:「本研究發現,瞿秋白的思想其實是史華慈(Benjamin I. Schwartz)所謂的『將各種不同觀念新異地並置起來』(novel juxtapositions of ideas)的知識世界。無論在他前期還是中、後期的著述中,都充斥着錯綜複雜的思想雜交現象。」
張歷君參考了史華慈的「『雙方面』的辯證法」研究這種複雜的思想雜交現象:「瞿秋白前期的佛家思想與中、後期的共產主義思想重新交會起來,見證了各種古今東西的異質思想脈絡,如何出乎嚴整的學科界線之外,在『顛倒錯亂』的歷史時空裡交相糾結。為了更細緻地理解瞿秋白多重複雜的思想世界,我們需要一種同等複雜的思想史研究方法。」張歷君認為,清末民初在中國流行的「人生哲學」論述,構成了瞿秋白日後思想發展的基礎。民初中國知識份子對「人生哲學」論述的探討,並非單純地對西歐相關思想論述的被動接受,而是各種不同文化脈絡所產生的思想資源,在跨文化場域中的互動、對話和創造性轉化過程。
這本書一共分為三部份。第一部份「領導權與有機知識份子的形成」(第一至三章)重新考察瞿秋白(1899–1935)和葛蘭西(Antonio Gramsci,1891–1937)二人對「領導權」一詞的詮釋和用法,並進而勾勒出「領導權」的理論形構與二十世紀初左翼知識份子的政治參與之間具體的歷史聯繫。第二部份「生命衝動、革命政治與菩薩行」(四、五章)着力釐清瞿秋白早期著述中的柏格森主義(Bergsonism)、佛教唯識宗和無政府主義的思想脈絡(這個課題一直被主流的瞿秋白研究者有意無意忽視),從而「細緻呈現和解讀瞿秋白多重複雜的思想世界」。第三部份「自殺之道」(六至八章)中進一步闡明,瞿秋白那種由創造進化論和辯證唯物論交織而成的歷史觀,如何決定了他的主體性形構;這種主體性形構又如何影響他在二十世紀初具體的革命政治處境中的種種抉擇。
書中内容豐富複雜,值得讀者仔細閲讀品味。在我看來,全書最有趣的部份,是在結語「『心』的兩面」。第八章中引用了瞿秋白在《多餘的話》中的一段自詡:
一生沒有甚麽朋友,親愛的人是很少幾個。而且除開我的之華以外,我對你們也是種不是完全坦白的。就是對於之華,我也只露一點口風。我始終戴着假面具。我早已說過:揭穿假面具是最痛快的事情,不但對於動手去揭穿別人的痛快,就是對於被揭穿的也很痛快,尤其是自己能夠揭穿。現在我丟掉了最後一層假面具。你們應當祝賀我。
文中說的「之華」,就是瞿秋白的第二任妻子楊之華。在她之前,瞿秋白的第一任妻子是他在南京認識,又要到上海大學聽課的王劍虹,丁玲的中學同學和密友。這三人關係非常密切。作為瞿王戀情的見證人,丁玲後來以三人在南京和上海的生活事跡作為藍本,創作了小說《韋護》。在張歷君看來,丁玲畢竟掌握了瞿秋白思想中關鍵的難題:鐘擺般的二元性格。在丁玲的眼裡,鐘擺的兩端便是「革命工作」和「戀愛」。在1924年1月26日的情書裡,瞿秋白談到他「內部矛盾的人生觀」:
我內部矛盾的人生觀,雖然有時使我苦痛,然而假使缺少矛盾中的一方面,我便沒有生命:沒有「愛」,我便沒有生命的內容,沒有「事」,我便沒有生命的物質。這兩者的最基本的矛盾衝突,構成了他「內部矛盾的人生觀」的基本形式。
而在1月28日的另一封情書中,瞿秋白承認自己的「愛的囚奴」,還坦白說自己一生的根本問題,就是「戀愛和社會的調和」:
戀愛和社會的調和,──我不過抽象的說,──本是我一生的根本問題,我想他們本是調和的,我自己不敢信,要問我的「心」,「心」若給我一個承認,我可以壯壯氣往這條路上走去。自己的「心」都不肯給我作主,誰又作得主呢?”
這裡所說的「心」,其是就是王劍虹。瞿秋白常用「夢可」(法文「我的心」〔mon coeur〕)來稱呼她。張歷君指出,這段文字說明瞿秋白認為,唯有愛情的絕對律令,才能讓他把戀愛和社會兩端重新調和起來,並解決他自己内在矛盾的「人生問題」。而瞿秋白還相信,唯有將外部的世界徹底轉換成「一個共同相親相愛的社會」,人類的「生命」和「自由」才得以落實,而「這一點愛苗是人類將來的希望」。也就是說,愛是「一個解除了一切規律、自由放浪、相親相愛的波西米亞社會」,或曰理想社會存在狀態的基本連結原則。
但是,正如張歷君所指出,這種理想社會和存在狀態,明顯與「歷史工具論」的革命理論相違背。他對這種兩難公式有此描述分析:
要成就革命和解放,革命者便得完全否定個人的自由,將自己徹底異化成「歷史」和群衆運動的工具;然而革命者參與革命的最終目的,確實為了實現自身波希米亞式的自由欲望。如此一來,我們便得到一個永遠無法化解的悖論公式。這個公式所形成的鐘擺運動,貫穿於瞿秋白的一生,使他永遠無法擺脫内心的煎熬。
《瞿秋白與跨文化現代性》一書好看之處,不僅在於描述了恢弘複雜的跨文化場域,還在於揭示了瞿秋白的内心世界──在愛情之心與革命事業之間,瞿秋白無法取決,於是一生都處於躁動焦慮,在兩極之間做鐘擺運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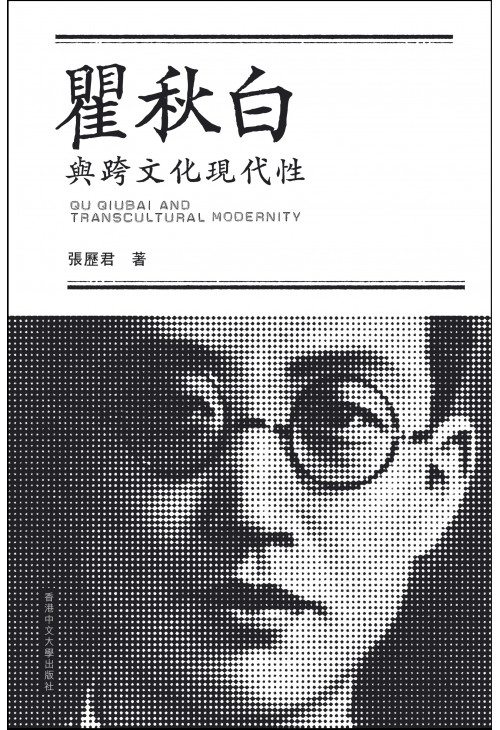 《瞿秋白與跨文化現代性》
《瞿秋白與跨文化現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