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心思脫離人類,嘗試學習像我所捕獵的動物那樣地思考。
──約翰.海恩斯(John Haines)
去年年中,我在北角森記二手書店閒逛時,找到約翰.海恩斯的《星星、雪、火》(The Stars, The Snow, The Fire),副題是“Twenty-five Years in the Alaska Wilderness”。因著對生態攝影家星野道夫的熱忱,每次看到與阿拉斯加有關的書籍,總會拿起翻揭,也對《星星、雪、火》這種簡單而充滿聲色氣味的書名帶著一份單純的好感,只粗略地讀了目錄,便買下了。記得大學時期讀過講述土地倫理,生態平等的自然文學經典《沙郡年紀》,對於 Aldo Leopold 細緻的觀察與對待自然時樸實的感性非常深刻,尤其是他在書中談及人類對於其他生靈消失的無感:「或許是殘忍的天意使然,讓幾千種動植物彼此殘殺滅絕以產生現今的世界,卻未讓這些生靈意識到這樣的歷史。而現在,我們同樣毫無所感,或許是出於天意。最後一頭野牛告別威斯康辛時,幾乎沒有人感到悲傷。同樣,當最後一株羅盤葵追隨那頭野牛前往夢幻之鄉──那綠意盎然的大草原時,也幾乎不會有誰為之哀泣。」與當時比較,現在的情況當然已經有了不少改變,生態與環境保育的議題愈來愈受社會大眾關注,然而對自然真正的尊重與了解,來自在日復一日的緩慢生活過程中,對謙卑的學習和不斷的實踐。
約翰.海恩斯在大學期間修習藝術,1947年夏天第一次定居在阿拉斯加的理查遜(Richardson),一直待到隔年秋天才離開,及後在1954至1960年代後期重返阿拉斯加,待了十二年,然後再次離開。等到下一次重返時,定居八年,他在序中提及副題中那「二十五年」所暗示的,「充其量只是代表許多來來去去的一個象徵性數字而已」。他在那個地方以採摘藍莓、打獵和設置捕獸陷阱等自給自足的原始生活方式度過這拼湊起來的二十五年,每當畫作因低溫而結冰,他便寫作,不僅是散文札記,還有詩。他坦言,本書是在這些事件過了許久以後,在不同的地方寫成的,作者重新經歷自己筆下敘述的各種片段時,感覺自己「似乎漫遊過許多歷史時期、地質年代和心靈狀態,而這些總是會回歸到一個源頭,一個獨特又完美的地域。」這個地域與空間,必須與時間連結,才能讓人在回顧時了解其相應意義:他在某個冬天設置的捕獸陷阱,他在山中遇上那頭狂奔的熊,他在酒吧遇上的老人,他聽見他們所說的故事……作者說這本書「是關於時間的──是關於人的時間感,以及某些事件發生的時間」,這個時間「無法以曆年的任何總數加以適當地表達」,他在阿拉斯加過度的日子,他所敘述的情節和事件,都如他自己所言,「存在於一種古老部落所說的『夢幻時間』(dreamtime)」,當他說「在遠古、遠古的時候」,他「不是在使用一個修辭學的說法」,而是因為「那些在原野上的日子、那些在雪地上、草地上和狗展開的旅行、那些長時間的狩獵、動物的屠宰,以及其餘的一切,都是這個地球上最深刻的人類經驗的部分。」
居住在城市裡的我們,對於這些古老經驗的喪失,也許無感,我們尤其易於相信:這與我們無關。即使這顯然是一個謊言。因為城市表面的璀璨繁華製造了一個如此巨大的幻象,供人們信仰,讓人即使置身於某種不幸之中,仍能相信那虛幻的「美滿幸福」,並以此作為真相,且成為他們窮其一生追求的依歸。這是城市對我們的欺哄,亦是由我們的無知、愚昧和貪婪所催生的產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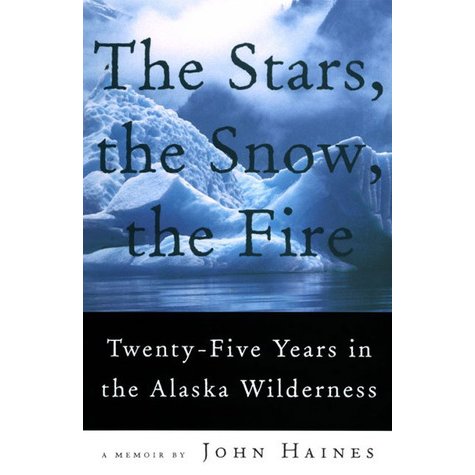
海恩思在書中記錄了他在阿拉斯加的生活,以札記的形式,分為十八章,內裡充滿著他的捕獵記事,遇上狼與灰熊的日子,對自然的熱情,生活的艱難,對雪的觀察,生靈的溫柔與神秘,他敘述著別人的北地故事,奪走生命的儀式,生存的謙卑,焚燒豪豬的回憶,出生與死亡。這些經驗模塑了他的生命,演繹著他所度過的年日,那是屬於時間的鑿打,我們無法避開時間,卻能模塑生活,或至少,擁有模塑生活與經驗的自覺與想像。
在《星星、雪、火》之後,我斷斷續續碰到便宜的梭羅散文,在精神書局遇到《湖濱散記》,然後是雨和森林的書。……散步、阿拉斯加、鳥、原住民、荒野、鯨魚、海、森林、月亮、雪、石頭、極地、光、早晨……這些對我來說猶如刺點的詞組,隨著年月和經驗變動,或是增加,或是減少,或是轉化,然後消失。有時伴隨氣味,有時伴隨聲音,有時成為像石頭一樣沉實的路標,有時則撼動猶如一個星系的挪移。上月讀畢吳明益的《家離水邊那麼近》,讀的時候正值初秋,讀至書末那張閃亮的書單時,腦內頓時出現一幅這樣的圖畫:他身穿輕便行裝,帶著簡單的背包,足夠的食水與乾糧,還有一本書,筆記本,一枝熟悉的筆。他用雙手觸摸岩石,青草,雙腳穩重地走在這個在他面前展開的世界,並一無所知地,決心學習。
像海恩思那樣,用他冰凍的雙手,在雪中設置陷阱,然後學習,如何殺死一隻狐狸,如何理解死亡與生命。在《星》的自序裡,他以此讓人深刻的話總結:「然而,我們無法憑著意願回到某些經驗、心靈狀態,和生活方式之中。我們與動物共同分享的世界,以及我們和一切存在的事物的原初的互動,這些當下的感受與經歷一旦過去了,很少能夠帶著令人信服的力量回返。實地的觀察和研究,無論多麼敏銳和詳盡,也無法取代它,因為經驗無法被制約成抽象、公式和說明。經驗是繁茂的,散發著血腥和被宰割之肉的氣味,混合著分量不等的恐懼、危險和喜悅。只要它能夠被稱為『經驗』,而不是其他已被遺忘的名稱,那麼,我們就必須屈服,雖然很少人會喜歡這種屈服。然而,在我們和自然相遇的短暫澄澈感和激烈感當中,在愛的行動當中,在回憶及重述一些本質性的情節(因為我們所關注的是一本書)當中,那些經驗的某些關鍵性時刻,是可以重拾的。生命的活力有賴於這些時刻,沒有這些時刻就不可能有藝術,不可能有精神定義,也不可能和這個世界發生真正的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