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那些對理論不感興趣而且其實也不需要理論的觀眾而言,讀到一些專業的評論時少不免抓抓腦袋:「象徵秩序」到底是甚麼來頭?這些理論又有甚麼大不了?對理論比較有認識的人則會認出,這個來自法國精神分析理論家雅克.拉岡(Jacques Lacan)的概念,經過如拉格勞(Ernest Laclau)、齊澤克(Slavoj Zizek)等當代左派學術明星發揚光大,已成為許多人分析性別、政治和意識形態的標準理論工具。但有了這重認知,我們還不免要問:由七八十年代以德希達(Jacques Derrida)解構、福柯(Michel Foucault)論述歷史分析為主的「後現代」文化研究,到現時深受拉岡那種艱澀、形式化(甚至數理化)影響的後馬克思主義左派政治理論,兩者之間的轉向理由何在?問題的核心在於,學術理論所關注的對象,已經由(大體上屬於)自由甚至放任自由主義的政治認知、關注浮游在(公民)社會裡形形式式的權力關係,轉移到「民主」這個政治體系本身。
誠然拉岡的講座在六七十年代的法國知識份子圈子中極受追棒,但他本人幾乎是一切巴黎左傾知識份子形象的相反(又或者是「鏡像」):Elisabeth Roudinesco為他寫的傳記中,把拉岡描寫成一個熱愛跑車、向病人開天殺價的分析師,他創立的精神分析學院也承繼了佛洛依德的傳統,極力維護當中去政治化的文化。拉岡的命運幾乎和黑格爾(G. W. F. Hegel)一樣:恰好是在世時的政治取態模糊,加上理論結構恢宏、有無所不包的野心,反而掩蓋了本人政治取態裡一些保守的元素,容許他們的理論遺產為左翼所挪用。[1]從此觀點看來,「象徵秩序」不過是重蹈「辯證法」這個理論概念的覆轍。
Warren Breckman的Adventures of the Symbolic: Post-Marxism and Radical Democracy [2]正是以知識史的角度,梳理了「象徵性/象徵秩序(the symbolic)」這個概念的前世今生,向讀者證明象徵界不止是二十世紀中葉法國結構主義的產物──那些以「語言學轉向」一詞匆匆概括過去的思潮發展──相反,「象徵」(symbol)這個概念本身就把我們帶回德國浪漫主義的思想:象徵和符號不同之處,正在於象徵指涉的是神秘主義的、不能以感官掌握的形而上真理和意念,而這點正體現在謝林(Friedrich Schelling)所言的「象徵正是藝術和宗教的內在連縏(the inner bond between art and religion)」(27)。當黑格爾將藝術和宗教視為絕對精神的發展之路上的其中一個要超越的階段時,他便預示了左翼黑格爾學派(以費爾巴哈為代表)對宗教的批判:在宗教的「象徵意識」裡,人仍然是異化的,沒有意識到自己的創造性。到了馬克思,象徵活動(包括藝術、語言、文化)更進一步的被勞動力和背後的經濟結構所統攝,貶為一種形同迷信的「拜物」。
但這本書貢獻最大、對現今讀者來說最有意義的地方,也許是Breckman展示出「象徵」從來沒有從此離開現代思想──反而,現代人類越是以為自己已經離開象徵的世界時,象徵的力量更是在生活中最受忽略的地方裡體現出來。這種觀點對要面對六八風暴的失敗的左翼法國知識份子來說,有著不容忽視的重要性。結構主義宣稱人只能被符號或「能指」所創造,它早就預言了革命的不可能;後六八思想因此把解放的可能性懸放到一個不可能達到的高點,要待到現今所有言說、象徵甚至存有的秩序都一併瓦解,革命才有可能。這點正是後六八的「後結構主義」中不同思潮的共同之處,由女性主義(Luce Irigaray)、反精神病學運動(Gilles Deleuze和Félix Guattari)、文本理論(Julia Kristeva、Philippe Sollers)和法國毛主義(Judith Miller)等均如是(130-131)。也是從這個時代背景出發,我們才能理解拉岡當時以至現在的吸引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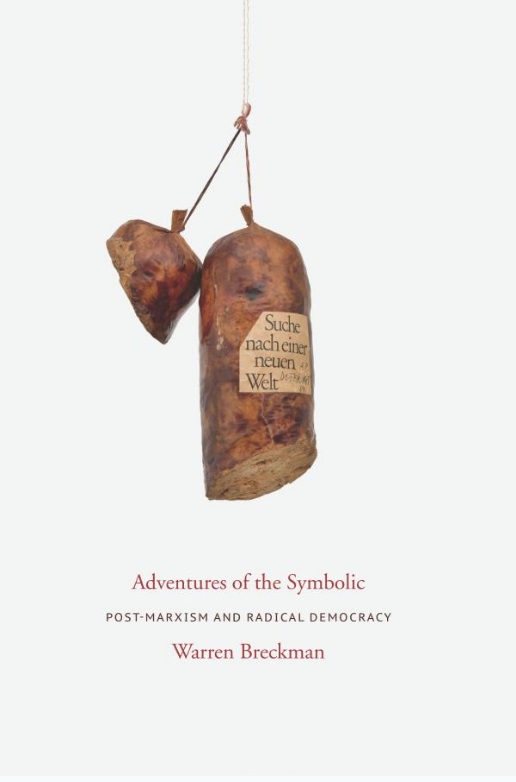
當然在這方面早有專著論及[3],而這點也不是Warren Breckman的重點。他的起點是Cornelius Castoriadis。身為法國裡最早對蘇聯的國家共產主義失望的知識份子,他也最先察覺到結構主義和馬克思主義裡命定論的元素,忽略人類作為具有想像力、能夠自我改變的動物,必然是創造社會的主體這一點。在他的社會理論裡,心理和社會歷史兩個維度都是「想像界」(l’imaginaire)的產物,它們互相影響但並不等同:社會意義來自群體想像覆寫原來屬於個體的想像,而這個過程中假定了一個真我與社會、潛意識等力量製造出來的假我抗衡。(在這裡,Breckman似乎認為以涂爾幹(Emile Durkheim)和摩斯(Marcel Mauss)為代表的法國社會學也許為「象徵秩序」這個概念提供了另外一個靈感來源:後人常說的社會「大他者」這個去個人化、以象徵顯現的「社會總體」,往往都隱含了摩斯以象徵界別思考社會實體的思想影子。)同樣,是想像「由無到有」的力量驅使Castoriadis和存在主義、結構主義、到宣稱「(大寫)人已死」的後結構主義等等法國思想流派保持距離,力排眾議的去思考人自主的可能性。在探討Castoriadis的一章中,拉岡大體上被塑造為結構主義的代表人物之一,和李維史陀並駕齊驅的成為Castoriadis批判的對象:拉岡的想像界(由鏡像階段為肇始)是異化和誤認的領域,也是欲望背後本體性的空乏的基礎;而Castoriadis強調心靈空間自我創造形象的能力,而這種能力本身便必然是處於無地之中的。
Breckman很快便指出Castoriadis批判的拉岡,不是後來啟發左翼思想的拉岡(138)。Breckman的敍事隨即轉向Claude Lefort,這位原來是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的學生後來轉攻政治哲學,「政治性」(le politique,相對於有界定邊界的「政治」la politique)一詞的用法也是由他開始的。(我們甚至可以說,在深深被所謂「法國理論」迷倒的學術圈子裡,Claude Lefort的重要性往往被忽略。)Lefort首先提出現代民主政體的創新之處,不在於實在的制度例如選舉或代議政制等,而是它把「權力」的位置騰空──因為「人民」本身便是不能定義的,任何佔據這個位置的人和實體,都只能偶然的擁有權力,而真正的民主正正就是把這個位置保持開放(至於極權則是宣稱這個位置可以被填滿)。Lefort從拉岡學到的是,構成人類「主體」本身的身份的,就是它的分裂──它的身份是無法圓滿實現的。Lefort將拉岡的分裂主體放到人類社會的層次,而現代社會正是反省地了解到自身的分裂,意識到社會的一體性已無法通過前現代本來存在的象徵(國王的神聖身體)體現出來,即為「權力/社會在象徵層面的去實體化(symbolic disincorporation of power/the social)」。這點我們將會在拉格勞(霸權的偶然性)和齊澤克(「大他者以外沒有大他者」)的理論裡再次見到;也正因這點,Lefort擺脫了施密特(Carl Schmitt)的政治神學(「現代政治概念不過是世俗化的宗教概念」),打開了真正現代世俗政治理論的空間。
Breckman觸角相當敏銳,察覺到在(當時還寂寂無名的)齊澤克與剛出版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的拉格勞和抹芙(Chantal Mouffe)之間最初期的交流裡,雖然大致上是互相欣賞的,但在那時雙方對拉岡在「後結構主義」裡的位置抱著不同的觀點,單憑這點已為二零零六年他們在Critical Inquiry期刊裡爆發的公開筆戰,埋下遠因。打從最初,齊澤克已經視拉岡為法國後結構主義裡的一個異數,在芸芸解離、延宕和分散的後主體概念以外肯定「主體」的存在(即使主體本身是自相矛盾的),並且在讀到拉格勞和抹芙的書中所說「社會場域是社會矛盾的角力場」之類的觀點時,非常受鼓舞的從中推敲出拉岡理論中「象徵秩序」和「真實界」之間的不可能性。然而拉格勞其實只視拉岡為後結構主義思想的其中一名要員,並且對齊澤克和他代表的斯洛文尼亞精神分析圈子裡對黑格爾的推崇備至頗有顧忌(208-209)。誠然,拉格勞雖然自視為將Lefort的「權力空位」理論深化的思想家,將注意力由民主「體系」移到建構民主「主體」身上,但在社會矛盾下,鬥爭者的角色仍然是「重新打開/形構民主權力的虛空」(238)。而齊澤克則堅持,「真正的革命」是勇於擁抱(不可能的)真實界:空虛的權位不單止事實上不斷被偶然的權力所填補(以至總能給左翼口實去抱怨「這不民主」),齊澤克宣稱超越(後現代左派的)自由民主政制的民主理論,正是要主動填滿這個權力虛位。而有這種能力的人由希臘悲劇的安蒂岡妮(Antigone)到雅各賓黨人,最後到「默西亞一樣的」列寧才得以圓滿。齊澤克投訴的是,左翼份子打從心裡不願意從外部攻克國家機構(the State)。拉岡理論裡的「小客體a(petit objet a)」、佛洛依德的「它物(Das Ding)」等概念,落在齊澤克手裡,就被用來解釋系統裡一些偶然、個別的元素如何昇華至代表總體、普遍的地位(224)。
和以前一些批評齊澤克「鼓吹暴力」、「擁抱極權」的聲音不一樣[4](儘管我們必須承認齊澤克打破了左翼思想在七十年代反極權主義思潮後建立的一重思想屏藩),Breckman非常盡力的重構了齊澤克的思想路向,指出了他由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開始投身在共產陣營陷落之後的後馬克思主義論述,從反極權主義思想出發到最後毫無保留地擁保革命狂熱的改變,這些改變有些是有意思的,但Breckman也看出有些的確只是前言不對後語(例如,齊澤克到底有多真心相信有甚麼元素可以真正填補象徵秩序固有的空乏?拉岡理論不是早就指出欲望的空乏是沒有東西可以圓滿的嗎?)。到最後,Breckman敘述的「激進民主理論」故事,到了齊澤克身上好像發展成一個自相矛盾的悖論:如果我們都同意自由主義民主不是民主的最終形態,那麼當齊澤克和其他激進政治理論家嘗試超越(資本主義式的)自由民主政體時,卻往往直認不諱他已經連「民主」都一併捨棄(240)。Breckman的結論落得相當精警:馬克思最初的資本主義批判,是以「為象徵祛魅」主導的,差不多兩個世紀,「象徵」這個概念被後人反轉再反轉後,當我們看到齊澤克在Revolution at the Gates中宣揚「我們就是要把馬克思主義當成世俗化宗教一樣擁抱」時,好像有些甚麼丟失了似的(249)。
Adventures of the Symbolic一書中尚有許多本評沒有論及但讀起來令人相當振奮的歷史爬梳:馬克思之前的十九世紀時在法國曇花一現的「浪漫社會主義」如何預演了後馬克思主義裡「象徵」和「真實」的辯證;梅洛龐蒂和讓.布德里亞(Jean Baudrillard)、阿倫.巴丟(Alain Badiou)、還有齊澤克與佔領華爾街事件。在Breckman筆下的這段歷史裡,讀者也看到西方左翼思想百川匯流的圖景:如果從我們最熟悉的那些支流上溯,便會發現來源正是我們很少聽說過的。對於飽讀「法國理論」但對法國知識份子文化認識仍有待進步的香港學術圈子來說,此書是不可多得的二手文獻,作者理論掌握仔細透徹之餘,亦不拘泥於無謂的理論陣營分歧,能夠在磨刀霍霍的理論大師背後,點出他們和他們所反對的之間的神似之處。對於在理論和實踐之間苦苦糾纏的行動者而言,這本書也可以有警世作用:在永無終極根基可言的現代政治世界裡,不管百家理論如何宣誥「自主」之死,自由仍然是可能的,而「民主不是解決的辦法,它本身便是問題。[……]民主派承認我們需要體制,同時覺察到民主的生機也超越、挑戰既定的形式[……]激進的民主派知識份子相信理論是有價值的,但也明白政治行動從不跟隨預設的指引。」(286-287)
注釋:
[1] 已有人依照「黑格爾左翼」的說法形容一些當代知識份子為「拉岡左翼」,例如Yannis Stavrakakis的The Lacanian Left一書。
[2] Breckman, Warren. Adventures of the Symbolic: Post-Marxism and Radical Democrac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3.
[3] 參見Bourg, Julian. From Revolution to Ethics: May 1968 and Contemporary French Thought. Montreal & Kingston: MQUP. 2007. 專論法國毛主義的亦有Wolin, Richard. The Wind from the East: French Intellectuals,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Legacy of the 1960s. Princeton &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4] 其中一例可見Gray, John. “The Violent Visions of Slavoj Žižek”.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July 12, 2012 Issue. http://www.nybooks.com/articles/2012/07/12/violent-visions-slavoj-zize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