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西九文化區重頭戲,M+當代視覺文化博物館二〇二一年十一月十二日開幕,免費對公眾開放一年,期間需要提前預約才能進場。西九董事局主席唐英年開幕致辭時表示,M+博物館可媲美紐約MoMA,倫敦泰特現代藝術館及巴黎龐比度中心,令香港由以前所謂的「文化沙漠」,變成國際文化藝術中心,有助推動本港文化藝術產業發展。
眾聲喧嘩的M+樂園
香港藝文界中的幾位好友,都在開幕式當天甚至前一晚已經在社交媒體上發布自己在希克展廳前拍攝的照片。我很想一睹為快,但在網站上預約了三次,都因為時機不合適,無法成行。所幸終於找到合適時機前往。那天早晨溫度驟降,灰暗蕭索。我坐巴士到西隧轉車站,跟隨指示牌走上天橋,首先經過故宮博物館的臨時辦公室,然後看到尚未完工的故宮博物館,之後經過自由空間,看到一兩個本地旅行團也在介紹M+。我從開闊草地一路上行到M+門口,找了兩個不同門口,最終得以在瑟瑟寒風中排隊,等候十點開門入場。排我前面的幾位女士衣著入時,五彩繽紛,據說從土瓜灣過來,遊離於隊伍裏外,雀躍嘰喳,不停拍照自拍。排在我後面的是陪着高齡母親前來參觀的兩夫婦,老太太至少有七十開外,一直在說風實在大,應該戴帽才好。而博物館保安人員打醒精神,對着大打蛇餅的人龍,一邊詢問是否有預約,另一邊提醒各人要掃安心出行碼,還不住地提醒帶着大包背囊的觀眾,要到另外一個門口排隊,如此等等。
在眾聲喧嘩之間,我不禁想起十多年前旅居歐洲時參觀各個美術館博物館的經歷。當時最喜歡去的城市就是巴黎,前前後後去過大概十次,把羅浮宮、奧賽博物館、橘園美術館、畢加索紀念館諸如此類逛了個遍,也曾在Shakespeare & Co. 書店流連忘返,在左岸舊書攤淘了不少寶貝。巴黎這個城市,對我來說永遠都是海明威筆下那一席「流動的盛宴」。後來看到Woody Allen發行於二〇一一年的電影《Midnight in Paris》時,總是會想起當年在巴黎街頭那種「被排斥在內者(include me out)」的感覺──既親切熟悉,又陌生失落。當年和好友去看龐比度國家藝術文化中心(Centre national d’art et de culture Georges-Pompidou),也是在十一月灰暗蕭索的這樣一天早上。那天清晨下過一點小雨,我們在第四區街頭快步行走,那潮濕落葉混雜淡淡煙草和咖啡味道,我至今仍記憶猶新。俗稱博堡(Beaubourg)的這幢四層工業風建築,鋼管結構縱橫營造出未來感,而蛇狀上行的透明管道則開闢出進入不同樓層的入口。開闊的地面空間上,觀眾三三兩兩隨意進入,也有幾個賣藝者,無懼寒風,熱烈表演。以入館體驗而言,可以說是最為親民隨性的一個藝術空間。龐畢度中心館藏之豐富,我個人覺得是要比後來去倫敦參觀過的Tate Modern要優勝的。而以建築和所在社區的融入感而言,我也覺得Beaubourg要比泰晤士河畔猶如紀念碑/工廠一般的Tate Modern,顯得更加入世。
好不容易進館,在竹製儲物櫃放下自己的背包,卻發現手拿電話銀包頗為不便,而且各種搭車行路排隊之餘,也已經覺得有點疲累,於是便決定先去UG的ATOR Creative Café at M+飲杯咖啡,補充體力,誰知藝術列印咖啡欠奉,咖啡店內有限的空間也已經滿座,只能隨意買杯飲品到室外小坐。原來這邊風景獨好,近看海邊單車徑跑徑,遠觀對面金融中心摩天高樓群。而最有趣的是,低矮布幕欄杆圍住咖啡舘室外空間,其實時常有人進進出出,和大門外人龍排隊,警衛森嚴的情景截然不同。喝了一杯熱飲,安定心神之後,我先在Café裏的紀念品商店買了一個M+標志的Tote袋,裝好自己的隨身物品,然後再靜心體驗一下館內的空間氛圍。地下一層的「潛空間」有些展品頗為有趣,比如九龍皇帝曾灶財的墨寶。專題展覽「香港:此地彼方」也是我想去看的,但門口排隊者眾,我決定還是先去二樓看專題展覽為妥。

乘搭升降機去到二樓,才發現原來 「亞洲的土地」 主題展外又是大排其隊,按照隊伍長度標識出等待時間,龍尾居然要排一小時才能進去展廳。這種熱鬧程度,我似乎只有在迪士尼樂園排隊玩機動遊戲時才體驗過。好在我的目標展廳是「M+希克藏品:從大革命到全球化」。這個展廳的外牆上,左側展示的是馮國棟的《光河》(1979),右側是張曉剛畫作《血緣──大家庭17號》(1998)。這雖是最多人打卡的地點,但也有不少觀眾純粹只是坐在椅子上休息而已。

「視角轉換」之下的生產空間
在M+希克展的展冊前言中,李立偉說明,
「M+希克藏品:從大革命到全球化」是一個專為香港策劃的展覽,…… 展覽中的八十多件藝術品只屬整個收藏的一小部份。而這個展覽也配合了M+項目的整體設計理念:
整個M+項目的核心理念,從某程度上講,是關於「視角的轉換」。我們用嶄新的角度,打破以巴黎,倫敦或紐約為主的思維模式,從香港出發,審視過去七十多年來全球各地的視覺文化包括藝術的發展。物轉星移,世界從此變得不一樣,連人們的着眼點也有所改變。舊有視角中的邊緣地區或事物,現在變得倍受重視,甚至能擢升為當代文化的中心焦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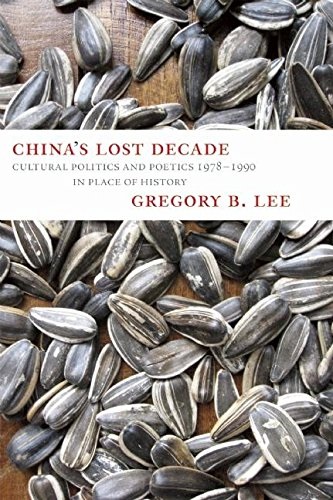 作為中國的政治文化中心,北京自然也是中國當代藝術創作的中心。在展冊上列出的藝術家簡介表明,大多數入展者目前的工作生活地點都是在北京。對於一個來自廣州的八十年代生人如我,其實是在法國里昂留學期間,才第一次聽到星星畫派的名字,第一次見到詩人北島。一九八五年,我的導師Gregory B. Lee教授正在北京大學做博士後研究,和星星畫派成員交往密切。在Diasporic Chinese這門課上,他和我們分享了很多當時拍攝的照片,當然也說了不少有趣的秘辛故事。後來,老師把這段經歷寫成一部著作《China’s Lost Decade: Cultural Politics and Poetics 1978-1990 In Place of History》,專門回憶這段經歷。
作為中國的政治文化中心,北京自然也是中國當代藝術創作的中心。在展冊上列出的藝術家簡介表明,大多數入展者目前的工作生活地點都是在北京。對於一個來自廣州的八十年代生人如我,其實是在法國里昂留學期間,才第一次聽到星星畫派的名字,第一次見到詩人北島。一九八五年,我的導師Gregory B. Lee教授正在北京大學做博士後研究,和星星畫派成員交往密切。在Diasporic Chinese這門課上,他和我們分享了很多當時拍攝的照片,當然也說了不少有趣的秘辛故事。後來,老師把這段經歷寫成一部著作《China’s Lost Decade: Cultural Politics and Poetics 1978-1990 In Place of History》,專門回憶這段經歷。
在這樣的知識框架之下,再看這個專題站對八五新潮,實驗團體寫宣言,辦展覽等活動的介紹回顧,自然有一種似曾相識但又距離遙遠之感。我坐在螢幕投影前,專心看了十多分鐘溫普林的作品《七宗罪──89年中國現代藝術展上的七個行為》(單頻道數碼錄像,時長52分鐘),介紹當年二月五日至十九日,由高名潞與栗憲庭等評論家發起的展覽。簡介如此寫道:
一九八九年,由藝術家自發組織的「中國現代藝術展」在中國美術館舉行,象徵前衛藝術從地下走向公開。由於行為藝術帶有顛覆意味,當時主辦單位禁止展覽中出現行為作品。然而開幕時,七個參展藝術家無視禁令進行行為展演,包括對自己的作品開槍的肖魯,此舉導致展覽瞬即被關閉。這些極富爭議的行為作品彰顯藝術家反抗體制的精神。
我所觀看的片段中,有兩幕尤其發人深省。第一宗罪是由WR小組發起的《吊喪》。三人小組之一的大同大張接受採訪時解釋為何要身披白布,在場內遊走弔唁前衛藝術,因為他認為:「前衛藝術不應向當局投降」。正是在這場展覽中,徐冰《天書》首次向公眾亮相。當年樣貌仍然有些青澀稚嫩的徐冰,在攝影鏡頭前介紹自己的作品《天書》,但也特意說明藝術作品、觀眾與作家的多重關係:「它變得渾濁而又瑣碎,他就屬於任何一個和他交流的人,藝術家與藝術作品是兩碼事,即意味着被他人利用。」
對我而言,觀看中國當代藝術四十年展覽,一方面是喚醒集體記憶的潛行時空體驗,另一方面也是探索當下生活空間與藝術關係的發現之旅。展覽中有不少引起爭議批評的作品,我也有注意,而且特別留意其他觀眾在這個展覽空間中對這些作品的反應,因為觀看者和作品的互動也構成了一種新的景觀(spectacle)。被挪用(appropriated)作為新的景觀的例子,可見於石心寧的繪畫作品《杜尚回顧展在中國》(2000-2001)。此幅作品被選用在M+希克展藏品展冊的封面上。M+網站對此作品介紹如下[1]:

這幅油畫以超現實的手法,把法國藝術家杜尚的小便鬥現成物作品《噴泉》與毛澤東並置在一起。石心寧這件作品所依據的藍本是一幅毛澤東參觀工業展的照片。畫中的毛澤東正在參觀《噴泉》,場景脫離現實,藝術家希望藉此探索「另一個中國」,想像如果中國歷史得到改寫,會出現甚麼不一樣的情況。石心寧的藝術實踐大多集中於與「文化大革命」有關的主題,自二〇〇〇年代初起,他的畫作以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表現方式,將毛澤東融入西方歷史事件。
法國新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家列斐伏爾(Lefebvre)在《空間的生產》(The Production of Space)一書中提出「生產空間」(to produce space)的說法。他認為社會空間是通過社會不同族群關係而再生產的過程,其形成有兩個組成部份,一個「感知的空間」(perceived space),另一個是「構想的空間」(conceived space)。這兩個軸所彙集形成的空間是第三空間,被稱為「生活的空間」(lived space),無法脫離空間表徵及空間時間的影響,如社會空間的共知(conceived)也會影響人們在空間裏的實踐與感知(perceived)的想法,這些觀點都與日常生活的身體與社會形成密切相關。[2] 在此意義上,M+希克藏品展廳(以及其相關網頁展示的藏品),提供了一個「第三空間」,將不同時空壓縮在一起,使它們交疊共存,為觀眾們提供了重新闡釋的能動性(agency),同時也成為了不同意識形態競爭的場域。
這種競爭性和多元性,在九十年代當代藝術展廳裏更為明顯。政治波普作品色彩造型的誇張吸人眼球,引得觀眾紛紛拍照,這也是自然反應。但與此同時,我也發現有另一種肉身慾望的狂歡,也許和意識形態無關。在九十年代當代藝術展廳還展示了北京東村藝術家們的作品。我觀展過程中,發現吸引最多觀眾駐足的,是張洹的攝影作品,《為無名山增高一米》,創作於一九九五年。畫框鑲嵌的照片中,張洹與其他藝術家在一座無名荒山上赤身裸體,趴成一堆。這幅攝影中,所有的裸體都水準向下,三點未露,入鏡者也以髮披面,無法辨認身份,鏡頭前呈現的多個身體堆疊,雖然猶如靜物,但其張力直逼眼前。然而,攝影作品和觀眾之間的緊張關係,卻被近距離探頭細看,然後舉起手機拍照的好幾位年老男性而稀釋。覺得行近尷尬而站在較遠處的我,有點想拿出手機,攝下這很有意思的一幕,但又覺得自己黃雀在後似乎不太厚道。此情此景,甚似詩人卞之琳筆下的《斷章》名句:「你在橋上看風景,看風景的人在樓上看你」。
這個小插曲,我在看展之後和幾個藝文界朋友聊起,他們都覺得很有意思,有點惋惜我沒有及時拍照,以便四十年之後加入這個展覽。其實,在我看來,這個小插曲只是說明了不同觀眾的立足點(positionality)在當代藝術作品展覽中的重要性。如果我們可以仔細看一下展冊中希克博士題為《我為甚麼收藏了這些作品》文章最後一段,就會更加明白策展者的用心良苦:
雖然中國當代藝術與藝術家的相關研究及學說仍在進行中,然而以更廣闊的全球性的當代藝術視野,將會在剖析中國當代藝術這個艱辛的研究過程中占一席之地。上述的收藏因素及考慮,與純粹以中國為中心的收藏策略有很大的差別。既然如此,毋寧順其自然。透過我在泰特(TATE)董事局和紐約當代藝術博物館(MoMA)董事局的參與,特別是與不少東西方著名策展人的緊密合作過程中,我知道我們的身份並非東西文化的代表,而是一個獨立個體。我們擁有的唯一共同點,就是各自對藝術的看法往往大異其趣。
旅行與觀看的意義
背着M+紀念標志購物袋,裏面是在紀念品店買的希克展圖冊,離開熙熙攘攘的舘內。走到外面,呼吸一口新鮮空氣,發現又是長長人龍。原來已經到了12點預約入場的觀眾排隊。我看到入口一側灰色外墻上白色M+字樣,於是決定還是全情投入做一回旅行者,請一位路人幫忙為我和這個標志拍照留念。「Been there, seen that, done that」 到此一遊,也就罷了。
十三年前的冬天,當時在美國讀社會學博士的好友,發來圖文並茂的十五頁PDF,寫參觀紐約現代美術館(MoMA)的體驗感受,其中有這樣一段:
Vincent van Gogh。《The Starry Night》。一八八九 年。六月。阿爾的清晨。它是一幅很小很小的畫,29 x 36 1/4″ (73.7 x 92.1 cm)。它沒有在 MoMA 遊客手冊的推薦名單上,所以那些頭戴耳機的人,急匆匆地走進展廳,走到編號的語音導遊指示牌前,遠遠地便按下放音鍵,一邊聽着介紹一邊上下打量,掏出相機來,呼朋引伴照相,然後急匆匆地奔向下一個展廳。卻沒有一個人停下來, 站定,安靜地,注視着這一小幅在角落裏牆壁上的畫,注視着它沉默而明亮的夜空,那片梵古曾經同樣注視過的溫暖的夜空,還有上面會眨眼的微笑着的星星。我的眼角突然便濕了。我強忍着,照了幾張相片,便沖出展廳,在樓梯旁,在那一窗的車水馬龍前,痛哭起來。二〇〇六 年十二月十八日下午三點半,紐約天氣陰沉,有小雨。那一刻我終於明白,原來,真的,會這樣。這是宿命的安排,或者說它就是宿命本身。 很多美好的東西,它的全部意義就在於,在某個時間,某個地點,讓某個你意外地遇見,然後讓你洗滌、淨化和拯救,自己的靈魂。 這是一種可以讓你一下子安靜淡定的美好。 只要你在此時此刻此地此間看到了它,之前的所有痛楚、悲傷、辛苦、委屈、輾轉,都再算不得甚麼。 原來,它們都是值得的。 原來,這就是我這次旅行的意義。
當年MoMA雖然熱鬧喧嘩,文青友人仍能偶遇《星月夜》,體驗難忘的覺醒時刻(moment of epiphany)。後來我留意到,五年前MoMA也開始展開一場名為「寧靜早晨」(Quiet Mornings)的運動。十月每個週三早晨,博物館會安排在線上預約購票的觀眾,在7:30至9:00之間,漫步在第四和第五層空間中,在放鬆閑適的氛圍下,慢慢欣賞包括莫內畫作《睡蓮》等的重要藝術作品,最後以在花園大廳的「引導冥想」課程而結束。[3]
而從二〇〇六年開始籌劃,今日終於開幕的亞洲首間全球性當代視覺文化博物館M+,又能否為匆忙緊張的香港帶來一個沉靜放鬆的空間?二〇二一年十一月二十日香港電台《香港家書》節目中,西九文化區管理局M+ 董事局主席羅仲榮詳細回顧了M+創建意圖和起名經過:M+此名來自二〇〇六年,博物館建設小組當時對取名莫衷一是,羅建議在報告書封面暫時寫下M+,M代表博物館Museum,而+即是plus。想不到後來報告書公布之時,這個名字因其寓意得到大家好評,於是沿用至今。這個名字是一個大膽的概念,寓意創造一間超越傳統的博物館。名字中+這個符號,意味深長,象徵建舘者希望此博物館能夠比傳統博物館具備更多的功能,除了構藏,保存,研究和展示藏品之外,也能夠與社會溝通,也能對社會大眾引起啓發,希望透過研究、教育、休閑和鑒賞,提高市民的質素。[4]
有鑒於此,也就不難理解為何今日M+會以免費開張一年的姿態,吸引着也許從未踏足美術館等文化場所的普羅大眾,在寒風之下仍熱切前來西九海傍,一睹各種藝術作品。這次匆忙結束的M+到此一遊初體驗給我最強烈的觀感是,戴着口罩的觀眾得以遮蔽自己真實身份和反應,和藝術品進行一種肆無忌憚的互動,既有一種街市趁墟的熱鬧喧囂,也有一種嘉年華身份倒置的宣洩快感。在這過程中構建出一種在地的第三空間,也可以說是共同創作的一種行為藝術吧。藝術為了藝術,人人皆可藝術,為甚麼不?
注釋
[1] M+,〈杜尚回顧展在中國(2000-2001)-石心寧〉。https://www.mplus.org.hk/tc/collection/objects/duchamp-retrospective-exhibition-in-china-2012913/。
[2] 具體討論可參閱此書英文版翻譯第32-42頁。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 Donald Nicholson-Smith (Basil Blackwell Ltd: Cambridge, Mass., 1991), 32-42.
[3] Moma, “Quiet Moring.” https://www.showclix.com/event/quiet-mornings/.
[4] 香港電台,〈西九文化區管理局M+ 董事局主席羅仲榮──以文化成就香港成為大都會〉,《香港家書》,https://www.rthk.hk/radio/radio1/programme/hklett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