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書寫經驗,大概能歸納為一種無可奈何。
我發現在音樂圈子內,不少人對語言文字有種距離感,甚至反感。又或者就是我們天生詞不達意,才有鑽研音樂藝術的原始需要。總的來說,我寡言,但從執起結他學懂四組和弦後就不斷創作,音樂上像有說不完的「話」要「講」。近二十年來,也好像真的未經歷過什麼叫缺乏靈感。只要有第一粒聲音,彷彿就聽到之後一連串聲音的排列,或同時間可以出現的和聲。然後思考節奏,速度,編排,就成簡單段落。段落與段落之間有一種音樂世界的邏輯,或靠着經驗直覺建構,要寫成完整作品,並不費力。邏輯經驗直覺多了,就開始製作實驗與噪音作品,顛覆已知,追求純粹的聲音的釋放。作家Elizabeth Gilbert說,文藝復興以前所謂「天才」(genius)並非指天生有才的人,而是像幽靈般隨處亂晃的意念,找尋適合的創作者成為容器(vessel),作品好壞與人沒太大關係,創作人也無須自負自卑。黃碧雲也說寫作過程像宗教經驗,人要「乾淨」,像通靈。這個意義下,我寫的音樂又好像與我無關,我只是努力練習如何聆聽這些空氣中的念,和抓住它們的技術而已。
英倫搖滾爆發的年代,我在英國荒廢學業,沉迷音樂。或者聽音樂才是我的學業。當時香港有位在中學時代開始自製獨立音樂zine的好友J,常要我推薦英美最值得注意的新聲;J畢業後在雜誌社工作,就邀我寫稿,因此我的寫作年資差不多與音樂同步,甚至更早成為「職業」。但和創作音樂不同,寫作並不容易,談不上享受,每每糾纏良久。尤其以文字書寫音樂,永遠覺得字彙不夠──能怎樣形容加州樂隊Deftones那乾燥焦熱得像太陽熔掉的結他聲?怎樣能準確描寫用耳機在街上聽Soulfly時彷彿能目空一切的氣勢?如何書寫把時間與空氣凝住,再爆發出來的各式各樣metal-core break-down段落?情緒被日本post-hardcore大團Envy用龐大聲壓翻動,起雞皮疙瘩的狀態,能如何讓人明白?或是像瑞典金屬名牌Meshuggah,用25/16的結他句子上碰撞4/4鼓擊,錯亂到反讓人覺得平靜的境界?我所有深愛的音樂類型,借文字再呈現時都變得無精打采,甚至體無完膚;但我更害怕矯揉造作的寫作方式,文字遊戲,離現實更遠。慢慢對樂評工作失去熱情,乾脆不寫。
猶記得回港後有次與朋友J看本地樂隊演出,談到自己剛組成的樂隊,如何四人夾錢買一包煙,如何儲錢搞band房,說到興高采烈之處,J竟然說:「阿珏,香港好多band,有二、三百人睇,就以為自己係大band,以為自己好型,你係咪想咁?」當時不知如何反應,但自那天開始總會不住自問,不想這樣,還可以怎樣?後來慢慢發現香港音樂界有一股怪風,不知怎地喜歡怨天尤人,流行歌手甚至乎會用上《音樂很窮》為演奏會命名;就連媒體也喜歡經常用「捱」,「堅持」等等框架去凝視,獨立樂隊是那種時事節目會想做專題報道的「社會議題」。比方說這個星期報道失業率上揚,上星期是香港淪陷結束70週年,下一集就是報道香港樂隊生態──沉厚嚴肅的旁述,鏡頭影着一班全黑服裝的長毛在用力揈頭,然後看到他們日頭打工,這樣的一個奇怪節目。如果這麼慘,這麼淒涼,不要玩就好了,有什麼好「捱」?阿根廷犯罪小說作家Enrique Ferrari說得好,其實很多勞動工人都寫作、繪畫或演奏音樂,這便是資本家及中產階段的特質:他們都認為工人無文化。Ferrari他本身就是名清潔工。

Sarah Marcus形容自己在找到Riot Grrrl時,情感同時得到定位,理解、釋放。我沒有這麼幸運,靈魂內擠壓着無以名狀的情緒,未能在年輕時接觸音樂當刻完全轉化;因為像Riot Grrrl一般,它不止於朋克形式,音樂與社會行動更是一個整體,存在抽象與具象兩面。因此對一頭栽進音樂的我而言,唯有多年後參與行動,回應藝術創作的無用之處,躁動才能得到救贖。如果音樂是我的藝術媒介,那作品的創作自述(artist statement),就是社會行動。
從加入民間電台開放大氣電波運動,合作營運無牌音樂展演場地Hidden Agenda,與友人組成「自然活化合作社」抵抗活化工廈政策,到爭取街頭音樂演奏權利、討論版權修訂條例、噪音條例、租金管制、IFPI無理索費、九東起動仕紳化、九西空降文化區等等,有數之不盡的音樂與文化議題留待我們去梳理。想起到馬來西亞參與藝術與社運研討會時,聽眾問到文化藝術工作者何以變成社運人士,我說原因很簡單,許多社會問題一直懸空,沒人肯碰,唯有自己解決。口口聲聲說熱愛藝術,熱愛音樂的人,除了自我滿足或自怨自艾,我們又為文藝土壤付出過什麼?在這個意義下,我對「行動者」(activist)這個標籤頗有意見:如此時代,「不行動者」(inactivist)不是更值得標籤、值得詢問其由嗎?
參與社運多了,被捕次數多了,如今音樂圈中人認為我是社運人,社運圈認為我是藝術圈的,藝術圈覺得我是band 仔,band仔認為我搞學術,學術圈又認為我是社運人。從前我對這種被擠拒於眾圈之外的狀態感到失落,甚至孤獨,但慢慢發覺這種身位與距離,是一種難得的獨立和自由。我們只是因為時代與自己的本位,去寫一首音樂、講一課書、寫一篇文章、擲一塊石頭。John Berger形容翻譯文章時,好的作家必須追尋先於文字的意念,抓住這無字之物,才能把意思挪動到別的語言。於我而言,創作、行動與書寫有着同一個靈,只是呈現方法不一。坦白說我從來都是個相當自閉的音樂愛好者,喜歡下午起床聽音樂玩音樂,直至翌日天光才睡;甚至乎對社會非常無知,好一段時間只依賴喜歡的樂隊音樂人去建構認知世界。就如好朋友梁寶山所言:「讀過書就係做呢啲嘢㗎啦」;作為玩音樂又識得幾隻字的人,只好硬着頭皮繼續書寫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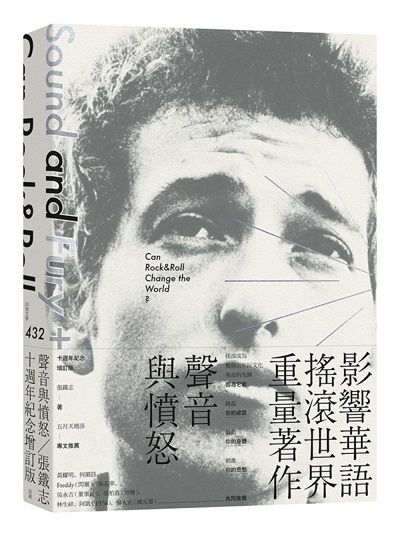
感謝楊陽與聲音掏腰包支持,有幸把數年間於中、港、台三地發表過的一些關於本地音樂、文化事態的言論與評論文章,結集增修成書。內容長短參差、文法簡陋,可以成書實在是編輯校對功勞。篩檢文章時,發現書寫過程中總喜歡有意無意地提起一些專輯,與它們如何影響着我的思考,於是很老土地於每篇文章之後選上一張專輯,或一齣音樂電影,讓讀者認識議題時有文字以外的參考,或只是像電台節目般恣意的為議題配調。為美術把關的設計師Lulu,竟然花上寶貴時間為每張專輯配上速寫插圖,實在喜出望外。感謝樓佳給予改進文章與多方面的寶貴意見。感謝梁寶山、小西、楊秀卓與眾多好友前輩,在寫作上的支持,感謝曾與我合寫專欄的梁偉詩答應編書。感謝認識於觀塘藝術區、特立獨行的文藝友好;特別是與我生活多年的Billy,邀請我到民間電台主持節目的梁穎禮,與及Zams、黃衍仁、年華、老B與郭達年等等藝術行動者,於不同時間影響着我的生命。感謝多年於不同媒體中成為我編輯的曹疏影,感謝張鐵志、黎佩芬等刊登拙文。
本書三篇序言,對我而言意義重大──黑鳥的《在黑夜的死寂中歌唱》、梁文道的《噪音太多》和張鐵志的《聲音與憤怒》,都是我的啟蒙讀物,邀得三位作者撥冗賜序是很大的福緣。長文多數寫於2013年以後,從嶺南文化研究系碩士畢業後的日子。鄭重感謝嶺南文研讓人再次相信教育,相信道理。如果讀者從書中選一篇最不知所云的文章,並與最言之成理的一篇(如果有)比較,那個成長差距,大概就是文研系老師們的工夫。
多年前,跟從新加坡專業混音師S學習,記得他說起數碼科技容許我們生產一些完美的聲波,也就是無瑕的聲音;然而,人們追求真空管擴音器,喜歡聽黑膠唱片等等的行為,是因為那些器材產生的聲音有「暖」、「真」的感覺,而這個感覺,其實是來自參差不齊,形似荊棘的波紋。現代電結他手當然明白這個聲色上永無止境的追求:我們能花上一生的時間,以不同樂器器材作媒介,尋找心目中最理想的破音──即是廣東話的「拆聲(caak3 seng1)」。這個追求,又與我書寫意念相同,故以《拆聲》命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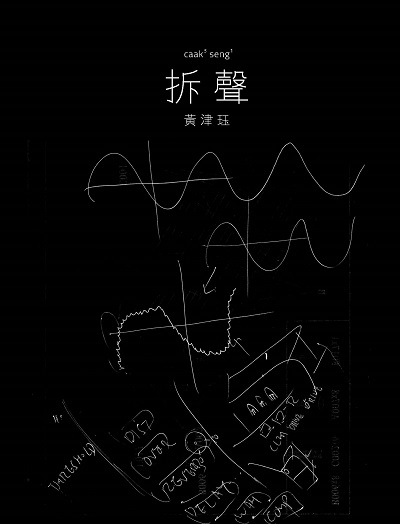
* 誠蒙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