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作活動首先意味命名。講述必須緊隨一個名字的經歷。
── “Barthes et les noms”, Alain Buisine
1915年11月12日,羅蘭.巴特於法國諾曼第瑟堡出生,自此開展了名曰「羅蘭巴特」的故事。大學時修讀古典文學與法國文學,其後健康轉壞,患上肺結核,因故無法參與高等教師甄試(agrégation),只能輾轉各地教授語言。1953年出版《寫作的零度》,回應沙特《甚麼是文學》一書的觀點。《神話學》(1957)收錄他於《新文藝》發表的文章,力求揭露大眾文化的面具,自此聲名日盛,着作越見頻繁。1977年,受傅柯推薦,破格獲選為法蘭西學院的文學符號學講座教授,並出版《戀人絮語》。年末,母親病逝。1980年,出版《明室:攝影札記》一書,二月出席一場午餐會後,橫過馬路時被貨車撞倒,一個月後因肺部併發症於3月26日病逝。
凡此種種,約略就是巴特一生的路徑了。數算下來,卻又彷彿不曾說過甚麼,即使把這些生平堆疊下去,也無從談論巴特的獨到之處,更遑論他於我的特別意義了。
在自傳《羅蘭巴特論羅蘭巴特》中,他在自己的生平年表後加上了一句括號:「讀書、生病、任職:如此過了一生。其他還有甚麼?相遇、友情、愛情、旅行、閱讀、樂趣、恐懼、信仰、歡愉、幸福、義憤、難過:一言以蔽之:一些反響聲?它們存在於文本之中──而不是作品之中。」是的,要談論羅蘭巴特,尤其是他無可抹消的痕跡,大抵必須經過文本的述說,這個幾乎與他無可分離的詞語;即使羅列他一生的傳記微素(biographeme),始終也無法迫近他特有的存在,於文本裡的種種表演。

◊
一位作家故去,我們的閱讀方式也會隨之改變,再說,正是這一變故打斷了寫作活動:若干本書由是變成了全部作品。死亡封存了一個文學生涯。但是,封存不僅僅是清點遺物的標記,它同時標誌一個起點:文本的新生命。
── Roland Barthes, Roman, Philippe Roger
沒有了,巴特在我出生前經已死去,我們的時間從未接合,他的全部作品已然完成,我只能重新潛入他封存了的作品之內。奇怪的是,每次讀到巴特的生平,友人為他撰寫的文章,總有一種近乎哀悼的情緒。人又何必為了一個非親非故的人而感傷?
這麼一個問題一直縈繞,往後為了理清思緒,每過一陣子,又會拿出他的《明室》重讀一遍。《明室》是巴特討論攝影的着作,與Susan Sontag的《論攝影》同屬早期討論攝影藝術的經典學術論著。其中,巴特談及的知面(studium)和刺點(punctum),幾乎是攝影論述中人所共知的術語了。雖是如此,坊間的討論卻常會略去了這兩個概念發起的原點。
巴特提出這組概念,原是因為沒法確認攝影的真諦,即使為其分類(人像照、風景照……),又或分析風格(現實主義、畫意主義……),也無法觸及照片的本質。由是,他就從個人角度出發,以自己喜愛的一系列照片起始,建設一套全以觀察者為中心的照片現象學。
因此,「知面」和「刺點」都需按此脈絡理解。知面指稱照片上文化與歷史的痕跡,客觀而毋庸置疑,觀者可從而得知一些「知識」,確認當時的衣着潮流、時代背景、文化資訊等;而刺點則是散落於照片上無關痛癢的細節,突然從照片表面如箭穿射出來,刺痛觀者,此刺痛的感覺多是起自個人的歷史,有時關乎一些往昔的感傷,無涉他人。如是觀之,就知道這組概念不可能解作放諸四海皆準的通則。最重要的,畢竟是主體觀照的即時感受。巴特作為觀察者,正是因為在某些照片裡遭遇刺點,才會起念深究攝影的真諦。不是將之看成需要處理的問題/題目,而是出於「感性的原因」,視之為「傷口」;觀察照片,進以研究,實是為了探尋自己欲望的軌跡,不以冷靜理性的論述把情感化約、收編。
巴特放在眼前的照片中,最核心的一幅,就是母親幼時於冬景花園攝下的一幀光影。在這張他名曰Winter Garden的照片裡,他從母親兒時藍綠色的明亮眼眸中,重新認出、尋獲母親的一切特質。沒錯,在目光之中悼念亡母,正是《明室》的原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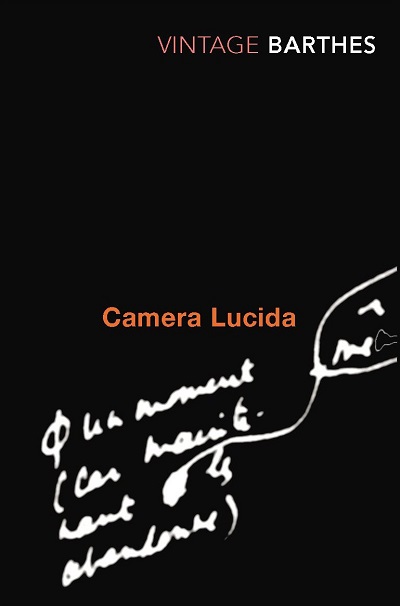
◊
有人說:時間可以使喪傷平復──不對,時間不能讓它消散,只是讓喪傷的激動過去罷了。
──《哀悼日記》,羅蘭.巴特
《明室》面世不久,巴特碰巧也離世了。由此,就難以避免轉喻的效果了,巴特以文章追憶母親,我們也在書中念想巴特。巴特的思想總是一直滑移,一再逃開任何的界定方法,後世老是苦於確立他於思想史中的位置。不過,對我來說,他正正是專職於探索個別事件的哲學家(Philosopher of the Particular),總是從一些偶然、意外之中閃見美麗的碎片,憑藉個人的喜好,靈巧地寫出這些特異之處的存在價值,堅守每一個主體的獨特視角,Derrida也說過,巴特一生不曾抗拒愉悅;由是我想,他與母親交疊的死亡,雖然不幸,但他會喜歡這樣的意外。
《明室》所論述的刺點,正正呈顯了巴特的獨特視角,如何從一張照片難以解釋的細節通往照片的本質,同時也借此隱埋了對母親的哀思。
細究刺點本身的定義,punctum是拉丁詞,指創傷、刺痛,用帶尖的工具造成的印記,也指小孔、切口、小斑點,甚至擲骰子。這些創傷、傷口、切口,其實統統指向一個母題:缺失(lack);照片中一些意外的細節,突然飛躍出來,又一次提示觀者,此物已然缺失。
創傷,可以是wound,也可是更深層的trauma。它指認人生中的一些事件,過後不管如何努力,也無法好好回應、表述,消化以至收編。主體由是只能一次又一次的重演相類的場景,試圖應對問題。佛洛依德着名的“fort-da”遊戲,正好闡明了這一點:某天,他發現一歲半的孫子Ernst執起了一個線圈,不時將一頭丟進床舖裡,又扯線收回來,丟出去時喊「fort」(走了),收回來時又興奮地叫「da」(在那裡/你看)。他認為,孩子正是以遊戲模擬母親離去和回來的情境,慢慢平復、消化母親首次離他而去的創傷。
巴特反覆在刺點中看到的,許是創傷的各種轉喻了。那一幀Winter Garden,雖然統涉全書的內容,在文本中饒有形體,偏是唯一形容過卻不曾於書頁出現的照片。這正好就是缺失的特質了:代表空洞,卻又讓萬物得以運轉,彷若銀河中心的超重黑洞。母親不在,是以無所不在。他是這樣解釋的:「我不能展示Winter Garden那張照片,它只為我一人存在。於你不過是一張無關緊要的照片,『平凡』的千百種呈現之一。……對你而言,不成傷口。」
在巴特眼中,照片無限地複製存在中只能發生一次的事,特質正在於它是絕對的「個別事件」(Particular),最高的「偶發性」(Contingency),獨此其一(This),也正如Lacan所指的Tuché,一次特殊的遭遇,如命運般降臨,讓人面對難以言表的真實。
母親死亡的陰影一路延伸,他繼續追溯下去,終於在一張照片中得到感悟:黑白照中,一位名曰Lewis Payne的年輕人靠在牢房的牆上,看着鏡頭上方不定的一點⋯⋯Lewis Payne試圖刺殺國務卿W. H. Seward,被判死刑,相中的他正在等候死亡。今天他已經死去,當時他也即將死去,快門咔嚓一刻,他正好卡在兩個時態,兩次死亡之間。這就是刺點的第二重意思了:時間。照片將事實攝下,全無保留,觀者卻又在其中驟見時間的痕跡,預示相中人終將死去,由此一切照片皆沾上了死亡的氣息。重看Winter Garden,看着母親兒時的身影,他對自己說:「她將要死去:一如精神官能症患者,我恐懼,恐懼一樁已然發生的災難。每一幀照片正是這場災難,無論相中人是否已然故去。」
此一伏筆,早於巴特確立以觀者為中心建構理論之時已然寫定。三個詞語觀者(Spectator)、景觀(Spectacle)、幽靈(Spectre)原是一脈相承。在照片中看見的,正是逝者一再歸返的身影,統統透過目光連結、流轉(三者均出自拉丁詞specere,意指觀看,轉而成為影像、幻像)。即使相中人尚未死去,相片一經攝下,也無從躲避、否證死亡的可能。
照片的真諦簡單得過份,就是「此事曾經發生」(That-has-been),我們無法否定,銘刻在底片上的,毋庸置疑地是自相中人身上反射而來的光線。如是,照片就是現世的memento mori了,不容否證一個人的存在,死亡的陰影卻時刻伴隨。尤其在照片之上,死亡變得平板,無可評論。死亡,最可怖的莫非如此:對於最愛的人之死,對於她的照片,我無話可說,即使參詳多久,照片僅僅指認「此事曾經發生」,沒法抵達甚麼結論。巴特無話可說,只能略帶調侃地表示,面對無語,他唯一可以做的,就是談論「無話可說」的狀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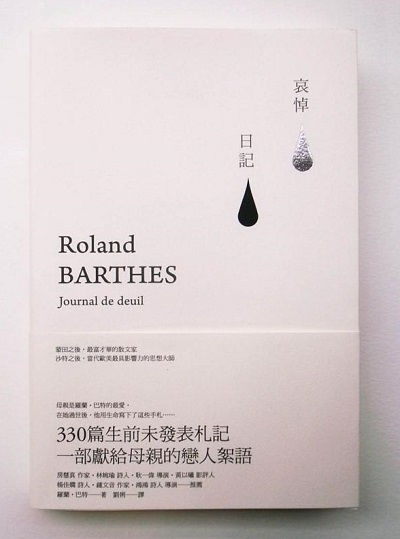
◊
不是將喪傷(悲慟)消彌(以為時間可以療傷的愚蠢想法),而是改變它、轉化它,將它從一種靜止狀態(困厄、悒鬱、不斷重複的相同情緒)變成一種流動狀態。
──《哀悼日記》,羅蘭.巴特
沒錯,一個人又何必為了非親非故的人而感傷呢?巴特對母親的哀思,畢竟出師有名。我卻一直數算不清,自己因何迷上「巴特」這一名字牽繫的一切,以至為何妄談哀悼。
不過,我卻總是記得,那一次在網上看到Julia Kristeva的講課影片,突如其來的驚詫:「這雙眼睛曾經親眼見過巴特。」Kristeva曾是巴特的學生,把Bakhtin的理論帶進法國知識界,巴特的文本理論也受此影響。《明室》本身,也是以相似的事情開展的:巴特偶然看到拿破崙最年少的弟弟的照片,驟然驚覺:「我看到的這雙眼睛,曾經見過拿破崙大帝。」影像一再轉喻,從一道目光轉向另一道目光,途中卻也滲染了《明室》之後探索的主題:刺點、時間、死亡。
自此,讀過許多巴特的傳記、生平,友人為他撰寫的悼文,諸如Sontag的〈緬懷巴特〉、Calvino 的Collection of Sand、Derrida的The Work of Mourning,試着從別人的文字中重新尋見巴特的殘影。雖然,終究是沒法清楚了解,巴特之死到底掀起了我何種欲望,至少也在諸多文章裡窺見折射而至的友誼之光。
悼文總是矛盾:對象既已故去,悼詞究竟植根何處,對誰人訴說?面對逝者,我們總是找不着適切的言語,然而沉默又形同背棄,視對方不置一提;讚頌、評價容易流於自私自戀,將他變形得不倫不類,只覆述他說過的話語,卻又近乎全無意思。悼念,若要忠實於逝者,幾乎是不可能的。
閱讀悼文,自也見出這種難言之苦,總是沒法子一針見血,直寫對象的特殊之處。要不沉悶囉嗦,要不彷如三言兩語便已打發,要不就是陳詞濫調,令一個人獨一無二的死亡事件流於俗套。常是顧左右而言他,不是誇飾就是貶抑,悼文就是如此進退失據,毫無分寸。
《明室》一書,也是一種側寫的悼文,其中提及母親的部分,偏是少之又少。參照《哀悼日記》,巴特在紙沿透露,《明室》是專為母親而寫的,渴望以此為她立下紀念碑,不求個人名聲,只願母名長存。雖是如此,書中的巴特即使不曾遮蔽自己的存在(全書不似普遍論着般避用「我」為主語),也沒有呼天搶地,哭喊母親的離席,情感是平緩的,書也寫得迂迴曲折,一路揭示探究的過程(常言「來到這一刻我的探究⋯⋯」),時而失敗,時而兜轉,卻總在一些缺口中閃現他深沉的情意,是至為感人的哀悼之作。
悼文如有真諦,或許就是源於執着,一再追逐主體心中逝者那難以捉緊的核心,甚至失卻焦點,顯得粗野笨拙,內容不斷兜轉。迂迴正正是悼文這一文體的形式,這一種形式,有時卻比一切的內容都更顯心跡;悼文注定失敗,而失敗更見忠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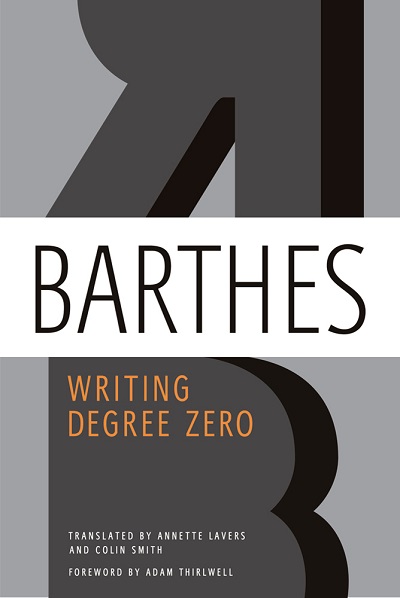
◊
要悼念一位思想家,重現他的力量而不違忠實,或許就只有一種方法:重複他的思想,讓他自行說話,任其再次流轉。
《明室》裡提到:「我的現象學同意與一種力量妥協:情感;情感正是我不想化約的事情」,也許正正顯露出整個寫作計劃,以至悼文這種文體的核心。悼念逝者,單靠理性,難免索然無味;只談感性,一如《哀悼日記》,悽楚固然明確,卻又不免失卻深沉。哀悼若然真切,就不是容讓理性的話語化約情感,將之馴服收編,處理得妥妥當當,封存起來,事後不再理會;情感的真相總是在東拉西扯,散漫離題的邊緣滲漏出來,悼文並無所謂「剛剛好」的狀態。
自母親亡故,到《明室》寫成一刻,也有一年半的時間,巴特堅稱喪母之痛不會隨時日消褪,頂多只是不再激動。喪慯不會平息,然而效果會漸次收減,原因自不是因為已然忘記,而是這一層傷口、這一重缺失已不再是外在己身的事件,改而悄悄移入,成了自己存在的核心,自此難以撇脫。
撰寫悼文,把話說得亂七八糟,又一次在文章裡、從照片中回顧喜愛的人的軌跡,追隨他的步伐,重複他的話語,讓他的身影稍稍顯現,一再面對這無以彌補的創傷,畢竟都是生者為了尋索逝者的舉動。迎難而上,接受失敗,繼續走下去,不作摒棄聊當安慰,許才對得起逝者。我會記得,巴特意外那天,擱在桌上那一篇最後的文章,題目正是“One Always Fails in Speaking of What One Loves”。
* 文章轉載自《Sample》第一期
